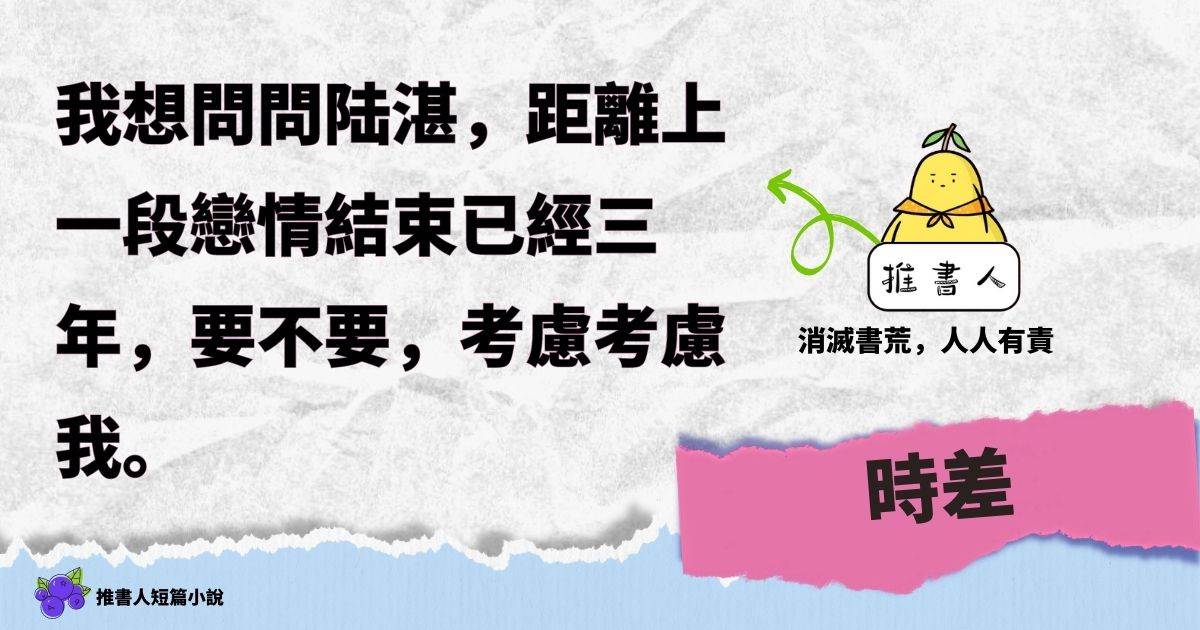《時差》第5章
屏幕上出現陸湛的臉,不知是在看鏡頭,還是凝視鏡頭后的我,笑意溫和,眼若星辰。
「在看什麼呢?這麼出神?」ӳž
宋予旸將礦泉水瓶貼在我臉上,冰冷的溫度刺激得我立刻回過神。
我接過礦泉水瓶,不理會宋予旸惡作劇得逞的笑,摁下關機鍵將相機收進包里。
宋予旸定是看到了那張照片,但是他什麼都沒說。
下半程的臺階明顯比之前陡,我爬得吃力,摸了把鼻尖,已經沁出一層細密的汗。
反觀宋予旸,倒是氣息平穩,如履平地。
「你看你,就是平時疏于鍛煉,以后還是得多出來走走。」
說不準是好心建議還是無情嘲笑,我斜睨他一眼,自顧自往上爬。
宋予旸快走幾步到我前面,然后他轉身面對我,向我伸出一只手。
「接下去的路,就讓我陪你一起走完吧!」他說。
火紅的夕陽映著身后沉穩的大山,宋予旸說出的話無端鄭重,鄭重到讓人以為他說的不只是剩下的山路。
面前向我攤開的掌心寬厚,只要把自己的手放進去,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溫度,剩下的路,也可以不用那麼累。
猶豫不過一瞬間,最終我伸手快速地擊了下宋予旸的手掌:「我自己也能走。」
宋予旸看了看自己的掌心,搖頭無奈地笑。
那天是冬日難得的晴好天氣,我們并肩爬到山頂,夕陽尚未沉入地平線,肺部注入清新的空氣,遼闊的景象讓心情也豁達了幾分。
8
新年前夕出了樁意外。
下班后我在大廳遇見一個患有精神分裂癥的病人,之前他住院了一段時間,病情好轉后出的院。
ADVERTISEMENT
他面帶微笑地向我問好:「舒醫生好,下班了啊?」
「是啊,你看起來精神不錯,最近有什麼不舒服嗎?」他表現得那麼正常,以至于我放松警惕,向他走近,像老朋友般跟他問候。
可他突然面色一變,雙目圓瞪:「都是你們,要害我,追殺我,還把我關起來!」
他說著,從身后拿出一根木棍,高高揚起。
就像慢動作的回放,眼看著那根木棍離我越來越近,就要砸向我的腦門,身體卻來不及做出反應。
電光石火間,一個大力將我推開,然后我聽見耳邊一聲悶哼。
宋予旸痛苦地靠在我肩上,半晌才緩過勁,從齒縫間倒抽了口涼氣。
病人清醒過來,拿著棍子呆愣在原地,一時無措,附近的保安迅速趕來將他制服。
宋予旸原本只是等我下班,因為這場鬧劇肩胛骨裂,需要在家休養一個多月。
一切都是因我而起,不由分說,我有一空就往他那邊跑,照顧他的起居日常。
除夕夜我媽和她的現任丈夫從外地趕來,陪我一起過春節,周阿姨邀請我們過去一起吃年夜飯。
我上大學時期陸伯伯突然向周阿姨提出離婚。
即便已經相伴過了大半輩子,剩下的時光也不愿委曲求全,陸伯伯承認遇見了讓他心動的人,愿意凈身出戶。
周阿姨哭鬧過,挽留過,但也不可能讓一個人回心轉意。
曾經那個溫柔愛笑的周阿姨像是變了一個人,她患上了抑郁癥,嚴重的時候嘗試過自殺,幸虧陸湛及時發現。Ϋȥ
所以三年前陸湛是萬不可能跟著夏蘇一起離開的,周阿姨需要人照顧,陸湛他走不掉。
ADVERTISEMENT
這些年周阿姨肉眼可見的消瘦,好在經過精心治療,精神狀態尚可。
餐桌上免不了又談及年輕人的婚戀問題。
周阿姨往我碗里夾了筷菜,又看看陸湛,笑容可親:「我們舒宜從小對阿湛什麼意思,阿姨都看在眼里。」
她伸手幫我把垂落在胸前的長發捋到肩上,「既然現在你們都沒有對象,就試著處一下嘛!」
真是猝不及防,一口菜就這麼哽在喉頭,我瞬間憋紅了臉。
我看向陸湛,以為他會主動解釋些什麼,可他只顧埋頭吃飯,完全沒有理會我們這邊。
「你看你,這麼大了倒學會不好意思了。」周阿姨笑嗔道。
「以前阿湛不懂事,我早就看出來,他和那個夏蘇不會長久……」
周阿姨還要繼續往下說,陸湛終于將視線投向我們,他沉著臉,還是什麼都沒說,只隨手抽了兩張紙巾遞給我。
我終于用紙巾捂著嘴嗆咳起來,也適時將周阿姨打斷。
9
飯后我到陽臺透口氣。Уȥ
「上次去看予旸,他說這段時間都是你在照顧他。」
陸湛站到我身后,他將手里的外套搭在我肩上,我掙了掙,沒能掙脫,只能由他。
「雖然他是因你受的傷,但你也不需要這樣親力親為地照顧他,給他找個護工得了!」
我被陸湛這種輕飄飄的語氣氣笑:「那夏蘇生病,你不也是照樣寸步不離地陪在她身邊?」
陸湛愣了愣,隨即勾起嘴角:「所以舒宜,你還是在吃醋?」
我曾經愛慘了陸湛這樣的笑,帥氣中透著點痞氣,可現在只覺得無語,不知道要怎樣打破他這種自以為是。
「我和夏蘇畢竟在一起過,就算沒了感情也不可能完全棄她不顧,她有意跟我復合,但是我發現對她已經沒有當年那種感覺了。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