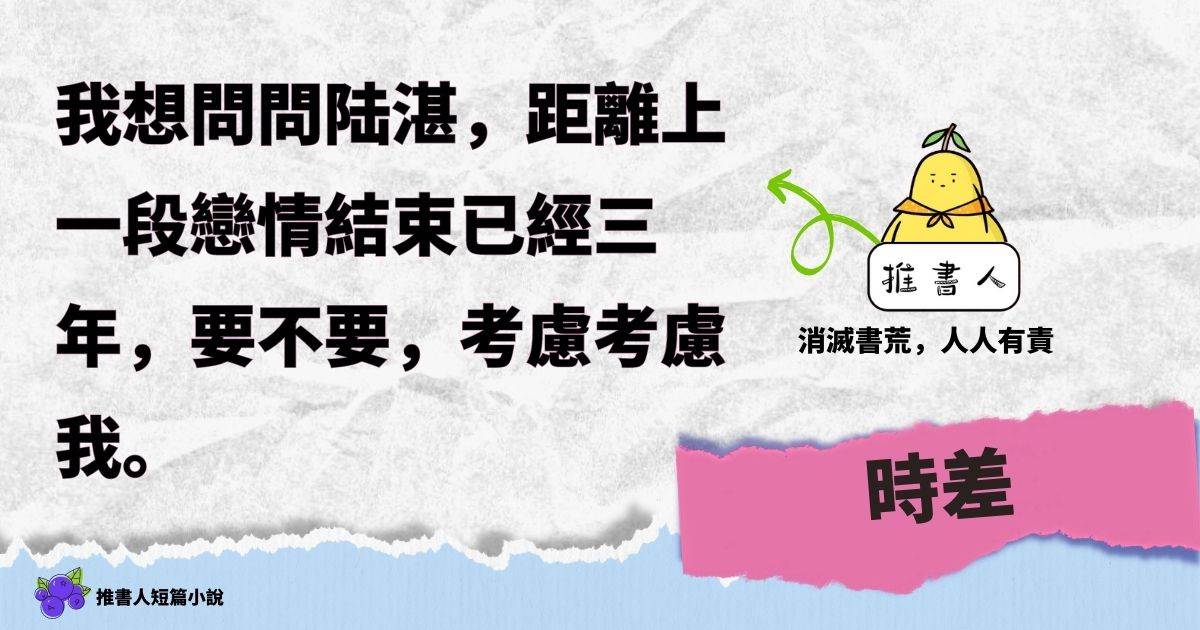《時差》第2章
」
夏蘇說著掩嘴輕咳了下,她往陸湛那邊瞥了一眼,帶了點嬌嗔的意味。
陸湛有些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對著我道:「我一開始沒在意,后來手機沒電自動關機了……」
他的眼下青影明顯,定是徹夜未眠,為了陪夏蘇。
陸湛走近些,在我病床前微俯下身,放柔了語氣:「現在好些了嗎?」
這又算怎麼回事呢?出于「朋友」的關心?可那種在意的眼神又難免讓人誤解。
我甚至想提醒他,夏蘇還在一旁看著呢。
她站在陸湛身后,面色略顯憔悴,但是掩不住本身的明艷精致,看起來有幾分楚楚可憐。
人在虛弱的時候連情緒都無法得體掩飾。
我只能撇過臉去看窗外,被子下面的手一下一下摳著床單,哪怕稍有不慎眨一下眼睛,淚水便會有決堤之勢。
我不知道夏蘇是什麼時候回來的,在我不安于陸湛可能出了什麼意外的時候,他整晚陪著夏蘇。
怪不得他接了電話就有那般焦灼的神色,我該了解,只有夏蘇才會讓他如此緊張。
所以他們是打算復合了嗎?
可我又有什麼資格和立場去質問?
我慶幸昨晚尚未來得及將那個問題問出口,不然就太難堪了。
「今早我聽見你手機響,看到顯示的是老陸的來電,我想你們認識,就通知了他。」
沉默的氣氛透出幾分尷尬,宋予旸適時暖場。
我這才注意到站在一旁的宋予旸,摘了口罩,眉目清俊,比想象中還要年輕些。
「謝謝你。」我對著他,由衷道。
陸湛還想說什麼,被宋予旸往病房外推。
「現在病人最需要休息,你們先回去吧!」
ADVERTISEMENT
陸湛只能作罷,臨走前拍了拍宋予旸肩膀,一副熟稔的樣子:「予旸,那舒宜這段時間麻煩你多多關照。」
「那是當然!」宋予旸忙不迭地應著,已經把人推出病房。
回頭往我的方向看了一眼,嘆了口氣,搖著頭掖上了病房的門。
該感謝他的邊界感,留我一個人獨處空間,不至于在人前暴露脆弱不堪的一面。
4
陸湛向人介紹說我是他朋友,或許找不到更合適的兩個字詮釋我和他之間的關系。
心有不甘的人是我。
第一次見到陸湛是十三歲那年,我媽和我爸離婚后,她帶著我回到榆城。
她帶我去見她的閨蜜,讓我叫她「周阿姨」。
周阿姨和我媽聊天,我便縮在角落看一本故事書。
窗外的蟬鳴,電扇葉發出有節奏的「咔噠」聲,交織成一首催眠曲,我靠在椅背上陷入酣睡。
朦朧間似乎有人在我身邊走過,帶起一陣微涼的風。
「哪里來的小孩?」屬于少年人的粗啞嗓音。
手上的書本掉落,我被驚得起身,眼前是一個瘦高的少年。
大概是剛打球回來,穿著球衣,兩頰的汗水不斷往下淌,些許墜落在木地板上。
「喲,吵醒你了?」少年將手中的棒冰遞到我眼前,「吃棒冰嗎?」
家庭的變故、陌生的環境讓我變得拘謹,而且我方才分明看到他剛要把那棒冰往自己嘴里送。
我怯生生地看他,抿唇搖了搖頭。
「喏,沒吃過的,你放心。」他又將棒冰往我面前送了送。
再拒絕就成了我嫌棄他似的,我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接過。
少年沖我笑,膚色曬得黑,牙齒顯得格外白,笑容明朗,就像清晨的微風。
ADVERTISEMENT
棒冰的滋味在遙遠的年歲中已然變模糊,但我永遠記得那種沁涼的感覺,拂去燥熱暑氣。
后來在飯桌上我得知那個年長我三歲的少年叫陸湛。
周阿姨特意囑咐他:「以后舒宜跟你一個學校,你要把她當妹妹,多多照顧她。」
陸湛一拍胸脯爽快答應,他也確實兌現了他的承諾。
剛轉學那會,我一時融入不了新環境,被孤立、被捉弄,是陸湛替我出的頭。
上體育課崴了腳,是陸湛背著我,把我送回家。
下雨天,是陸湛等在教室門口,給我送一把傘。
……
那麼些年,我已經習慣了陸湛的存在,也單純地以為可以一直這樣下去。
直到陸湛大二那年暑假,他說要帶我去見一個人。
喧嘩的火車站,我第一次見到夏蘇,她隔著人群朝我們這邊揮手,身材高挑纖長,笑容明艷。
陸湛說夏蘇是過來找他玩的大學同學,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來不只是同學那麼簡單。
我們三個人一起吃飯,一起看電影。
他和夏蘇在餐桌下牢牢牽住彼此的手,也在暗黑的電影院忘情地親吻對方。
陸湛把我當成鄰家妹妹介紹給夏蘇,可我寧愿他遺忘我的存在,獨自赴約。
在三個人的約會中我分明是多余的那個。
多余到無地自容,只能味同嚼蠟般啃著爆米花,盯著大熒幕。
電影講述的是一個女孩青春期開始的懵懂暗戀,最后也未能修成正果,只有我一個人看得認真。
我不敢發出一點聲響,怕打擾到另外兩個人,也怕一不小心就暴露了自己并不平靜的內心。
夏蘇是陸湛的初戀,原來情竇初開會讓人變得傻氣。
他會在給我講題的時候突然發笑,也會在用餐中途跑去陽臺講一小時電話,全然不顧長輩在場。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