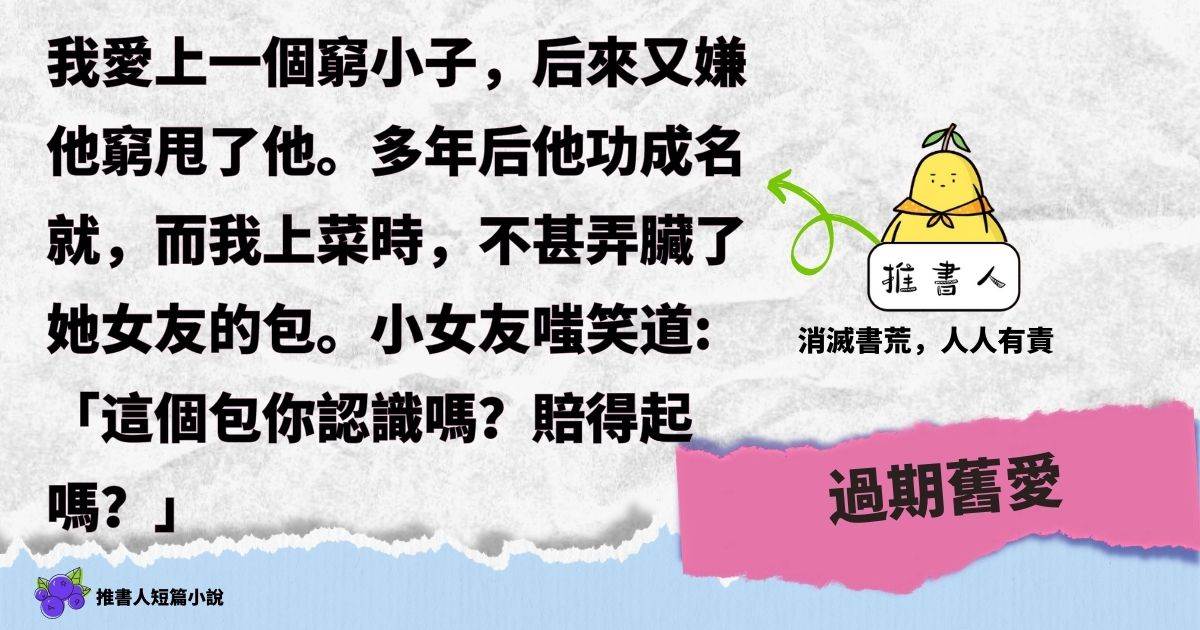《過期舊愛》第10章
「好無聊的問題……」我吐槽。
「那肯定是江承,謝川是前男友,江承在我心里像親人一樣,我還不至于那麼拎不清。」
「這不就得了。」
我:……
「爸爸,你們怎麼就這麼喜歡江承?你不是說男人大部分都不靠譜嗎?」
我追問老顧。
「男人靠不靠譜得靠時間證明,但是你跟江承在一起呢,我不是嫁女兒,而是干兒子轉了正。」
他認真給我分析著。
「最重要的是,你們在一起沒有婆媳矛盾,你受不著氣。那小子要是敢對你不好,得挨兩家的揍。」
「可我不知道我跟江承是友情、親情還是愛情?」
我爸無奈地嘆了口氣:「這個問題沒有糾結的必要,爸爸就問你,你跟江承在一起開心嗎?或者說,假如他從你生活里消失了,你們成陌生人了,你會不會難過?」
我爸就是我爸,每次跟他聊完,心里都能通透不少。
我躺在床上,心里似乎也有了答案。
只是沒想到,江承打來了電話,語氣還半帶威脅地跟我說:
「顧小蕎,你不答應我,咱倆以后就絕交吧,我見不得你跟別人好。」
我:???
「你威脅我?」
我一時人都有點懵,一氣之下。
「絕交就絕交!」
話說得雖灑脫,但吵吵鬧鬧這麼多年,也習慣了他那張破嘴。
真做了陌生人,一時想都不敢想。
12
第二天,我去見了謝川。
他先我一步開的口:「顧蕎,你是來拒絕我的嗎?」
我默默地點了點頭,沒再作聲。
他嘆了口氣,苦澀一笑:「其實,我自己已經想到了……」
他緩了緩,假裝釋然笑了笑:「顧蕎,能幫我個忙嗎?」
謝川的母親,癌癥晚期,已在彌留之際,想讓她走得安心一些。
ADVERTISEMENT
病床上的人極其瘦弱,頭發已然掉光,臉上沒有一絲血色,周圍是成堆的監測儀器。
多年前那個還在工地打工身強力壯的人,轉眼間竟成了這副模樣,心里一陣酸澀,忍不住地難受。
謝川輕輕地喚了她一聲:「媽,你看誰來了?」
床上的人緩緩睜眼,見到我后有些意外:「蕎蕎?」
我努力扯起笑:「阿姨,好久不見。」
她努力坐起來,半靠在病床,看著我笑得溫柔。
「小川,把你爸爸種的草莓待會兒給蕎蕎帶幾盒回去。」
她笑著拉起我的手:
「阿姨記得你最喜歡是草莓了是吧?」
我笑著點了點頭。
「阿姨,您好好養病。
「我和謝川,也會,好好的……」
她笑了笑,眼角里有些淚:「好好好……」
又轉頭吩咐謝川:「小川,你先出去吧,媽有話跟蕎蕎說。」
謝川出門后,她抹了抹眼角的淚,笑了笑:
「我知道,他是為了讓我安心,之前帶來一個姑娘也是,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沒放下你。
「可你這麼好的孩子,離開謝川,總會遇到更好的,這麼多年了,你們啊,怎麼還能回得去呢?阿姨雖然沒什麼文化,但這點道理還是能想明白的。」
謝川的母親拉著我的手,笑了笑又問道:「跟阿姨說說,結婚了嗎?」
「還沒有,已經訂婚了。」我忍住眼淚回道。
「真好,也不知道哪個小伙子這麼有福氣,阿姨只能現在祝你們新婚快樂了。」
隱忍多時的眼淚,終于在推門而出時,傾瀉而出。
突然想到小時候捉迷藏,爸爸明明知道我藏在了哪里,卻還是故意看看這里、看看那里,陪我演著幼稚的游戲。
這世上的父母,到最后一刻,都是在想著自己的孩子。
ADVERTISEMENT
「謝謝你,顧蕎。」
謝川站在我身側,拿起紙巾要給我擦眼淚,手頓在半空,意識到什麼后,又遞到了我手中。
我接過紙巾,道了句謝。
「其實,阿姨都知道,你想讓他安心,她也想讓你安心。」
謝川一愣,慌亂地轉過身,抬手遮上了眼睛,身體微微地顫著。
「她一直在瞞著我,每次電話里都說很好,她病了一年了我才知道……醫生說……沒有救……」
他努力地緩著情緒,聲音還是依舊哽咽:
「顧蕎,我們怎麼就到了要經歷親人離去的年紀了……」
我望著謝川的背影,思緒萬千。
「從前讀龍應臺的《目送》,所謂父女母子一場,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那時對這段話的理解還似是而非,只是莫名覺得傷感和無奈。后來才明白,人生不過是一場又一場的別離與遠行,沒有什麼來日方長,我們能做好的只有珍惜當下。
「其實,分手前,我回過一次家,那時我發現了爸爸的病歷單,他做了心臟手術,我卻從來不知道,真的覺得自己很不孝。為了愛情不顧一切,連自己父母生病了都不知道。所以這些年,我一直陪在他們身邊。
「謝川,你知道的,我不會說什麼安慰人的話,我希望……你能好好的……」
我望著他落寞的背影,突然間想起 18 歲初見的那個瞬間,年少的謝川,走在晚霞下,一身的破碎孤獨感。
片刻后,他緩緩轉過身,收起了失控的情緒。
「我們出去走走吧。」
13
他替我開了車門,白色的路虎,是那年我坐在他電瓶車后座,指給他的那款。
車里音樂電臺正播放著陳奕迅的《十年》。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