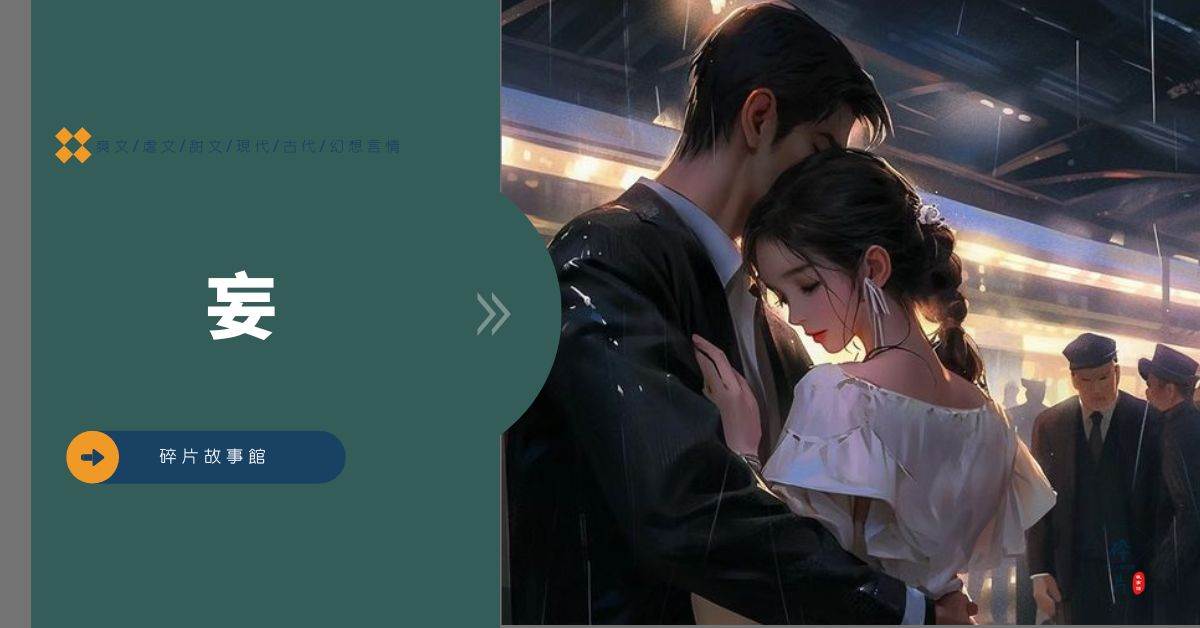《妄》第8章
我的同學和對面學校的女生戀愛跟過家家似的。
在一起快,分手更快。
他分手后,不再有聚會,不再能認識她。
只是我的學校放學比她的學校早,我在學校消磨時間。
回家時總是能見到挽著朋友手,蹦蹦跳跳放學的她。
感謝國際高中的高中部與初中部在同一校區。
姜緲初三畢業時,我已經認識她三年了。
第四年,她離開了。
我坐在校門口的長椅上,遠方夕陽漸落。
黃昏莫名蒼涼。
她去了哪所高中,會遇到什麼樣的人。
我不得而知。
人無法在過去的時間里窺探未來。
唯一能穿越時空的,是回憶。
我總是在無聊的時間里想起她。
分明我們沒有多少交集,分明她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但當小灰帶著她的孩子跳上我的膝蓋,當空氣里飄著淺淺的柑橘味道,我總是會想起她。
嗯,小灰是那只臟兮兮的小貓。
現在它成了老貓。
再下一次的見面又跳躍了幾年。
我畢業回國,她大二。
為大學捐款正巧捐到了她在的學校。
真是湊巧啊。
我在臺上講話,她在階梯教室的座椅上低頭擺弄手機,昏昏欲睡。
直到最后優秀學生代表上臺,我又聽到了那個藏在好多年前的名字。
姜緲。
她的室友推她,她猛地驚醒,動作看不出慌亂。
眼睛醒了,腦子肯定沒醒。
比如為我獻花時,眼神認真,實則神游天外。
她捧著鮮花揚起頭:「謝先生送您。」
又是匆匆下臺。
真遺憾。
我們又沒有成功認識。
好在她的輔導員我認識,我找她要了姜緲的微信。
輔導員當時看我的眼神很怪。
ADVERTISEMENT
她滿臉擔憂,看不出來在擔憂誰。
「姜緲那孩子,她心里門清,有點沒心沒肺,你要追的話,別抱太大希望。」
可不是。
她知道江遠希喜歡她,知道那個男生喜歡她,也知道我喜歡她。
但只要不明說,她就是個瞎子,什麼也不說什麼也不做。
姜緲對待感情不是遲鈍,而是一種天真到近乎殘忍的處理辦法。
暗戀在她身上,大多無疾而終。
我和她的微信對話只有一句「你好」,她沒回。
不知道是故意的還是忘了。
一位來捐贈的社會人士加女大學生的微信,能有什麼企圖。
她不是傻子。
我的勇氣也只支撐到這—句你好,后來再沒聯系。
估計是沒有備注,我被她打進了冷宮,多年后我們結婚重新加好友時,我才發現她早把我刪了。
作為捐贈的回報,我在這所大學掛了閑職,開了節選修課程。
姜緲選了這節課,一學期10節,她逃課8節,剩下兩節,一節是代課來上的,一節她全程在走神。
我氣笑了。
她沒有掛科全靠我仁慈。
她似乎還在學生之間宣揚,學校里流傳我的課絕不會掛科的傳聞。
第二次開課,那些和她─樣逃課的人全都掛科了。
不能怪我,得怪她。
我在她的墓前,對著黑白照說起這些趣事。
其實還有好多好多故事,她都不知道。
比如小灰一年前壽終正寢享年十七歲。
比如自大學起我與她的三百七十二次擦肩。
比如我們的相遇不是偶然是癡漢般尾隨后的趁虛而入。
本來想啊,我們有好長好長的以后,可以一件—件講給她聽。
命運向來喜好捉弄人。
無數次的分別與重逢,二十余載的好奇與暗戀。
通通被名為天命的手輕輕撥弄,破碎一地。
我在警局看見了兩個她。
一個躺在地上,一個飄在半空。
地上的她緊閉雙眼,半空的她哼著歌謠。
看起來很心情不錯。
真難想象,怎麼會有人死了心情還不錯的。
她真奇怪。
和從前一樣奇怪。
我在她的墓前放下一柬桔梗。
藍色的花瓣在搖曳。
略帶苦澀的香彌散在風中。
我合上眼眸。
早已消散的她在空中凝出一道泡沫的幻影。
姜緲在我的眼中對我微笑。“謝遲,你來啦。“
-完-
我是一個垃圾桶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