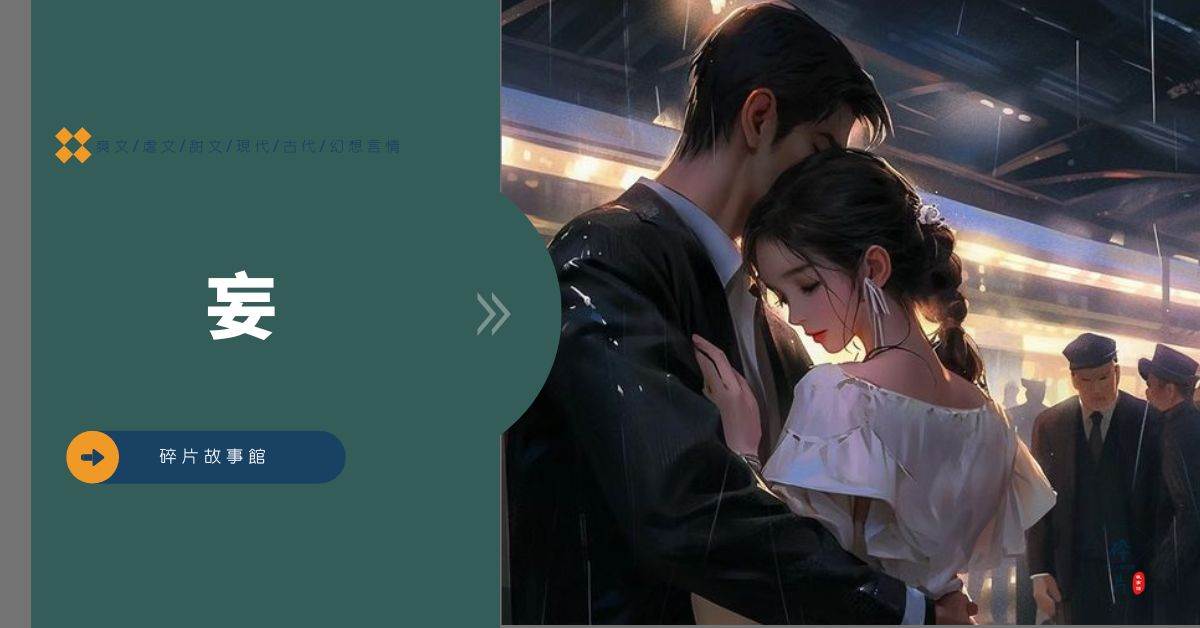《妄》第2章
我索性別過頭看自己的尸體。
死人白,僵尸臉,脖子上的水果刀被拔掉,留下一道猙獰的傷痕。
第三視角看自己可真丑啊。
「渺渺。」謝遲的聲音很輕,寬厚的手掌撫上那張蒼白的臉,重復進入警局的第一句話,只是這次換了對象。
「我來接你回家了。」
尋常的一句話,怎麼會讓人喘不過氣呢。
情感充沛的女警眼里毫無征兆盈滿眼淚,小小的眼眶裝不下淚水,啪嗒一聲砸在地上。
她手忙腳亂拿出紙巾擦,我下意識撫摸我的眼角。
指尖一片干燥,什麼也沒碰到。
就是嘛,死人怎麼會哭。
謝遲打橫抱起我,已經走到門口。
我回頭柔聲安慰女警察:「妹妹別哭,他帶我回家,這是好事。」
說完我不住失笑。
她聽不見。
所有人都聽不見。
游蕩在世間的亡魂,與生者隔著生與死的河流對望。
河面太寬,河水太急。
誰也抓不住彼此。
05
謝遲抱著我上車,原本壓抑的氛圍隨著空間的減少,更加致郁。
他話很少,此刻也不例外。
黃昏末尾,夜色初初籠罩大地。
城市的霓虹燈漸次亮起。
他沒有松手,寬敞的車后座一人一尸體,空曠得有些荒唐悲涼。
我飄在他面前,對著陌生人隨口說出的安慰話語,面對他,卻什麼也說不出。
車開啊開,穿越鬧市,穿過人潮。
清冷亮燈的別墅里,他將我放在沙發上。
客廳的電視自動開啟,他坐在我的身側。
就像我還活著一樣。
綜藝節目里嘉賓們在笑,電視機外觀眾面無表情在看。
謝遲忽然抱怨:「你為什麼愛看這種節目,真無聊。
ADVERTISEMENT
」
我不服:「哪里無聊了,這不是很有意思嗎?啊你怎麼知道我愛看?」
「姜緲你為什麼不說話?」
「我在說話。」
「是不想理我嗎?」
「我理你了!理你了!」
「你再不回答我,我換臺了。」
「不許換!你聽不見我說話怎麼還怪我,你好沒禮貌!」
謝遲轉過頭,對上我死亡僵硬的臉。
他一怔。
液晶屏幕的光芒好刺眼,電視的背景音好吵。
我差一點點就看不見他眼里蒙上的水霧,和那一聲道歉。
他在道歉什麼呢。
我伸出手,掌心遮蔽眼眸,回憶浸沒魂魄。
碾碎了一地的思緒。
06
謝遲沒有對不起我。
認識三個月,我們見面只有五次。
第一次是意外懷孕。
第二次他與我商討結婚事宜。
第三次是婚禮當天。
婚禮結束后,他對我微微點頭,語調柔和:「我住隔壁,有事可以找我。」
我松了口氣。
奉子成婚哪有這麼多感情,左右不過責任二字而已。
他愿意負責,我答應了。
僅此而已。
再多的夫妻義務,我……沒做好準備。
結婚后,來不及與他相處,公司一份出差調令落到我頭上。
我詢問謝遲的意見,他一句「這是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做決定」,我安心離開。
我出完差他出差。
我與他生前最后一面,是三天前的夜晚,他靠在吧臺邊,紅酒斟了滿杯。
空氣纏繞著微醺的味道。
他眉眼朦朧對我說:「你回來了。」
他從高腳凳下來,身子微微搖晃。
我正好奇他要去做什麼,只見他拿出空酒杯,為我倒了杯溫熱的牛奶。
「懷孕不能喝酒,要來一杯牛奶嗎?」
我眨眼,接過杯子。
這是我第一次離他這麼近。
他輕輕撥動老式唱片,吱吱呀呀流淌了一曲莫扎特。
ADVERTISEMENT
氣氛曖昧了起來。
他湊近我,酒香混合著甜甜的柑橘味道撲面而來。
香水味和他的氣質不太配。
我腦中剛升起這個念頭,忽地聽到他說,
「姜緲,你這個沒良心的。」
我楞楞抬頭想問他怎麼突然說我壞話,他扣住我的后腦勺低下頭。
這是我清醒時的第一個吻。
也是最后一個。
第二天他留下一句出差,慌亂離開帝都。
我將那夜的吻歸于第二次意外,打算等他回來問問他對未來婚姻的規劃。
都結婚了嘛,沒有感情也可以培養呀。
我們有一個寶寶,要一起過好長好長的未來呢。
可惜問題永遠問不出了。
吻別成了永別。
07
我抱著膝蓋,坐在自己的尸體旁邊。
好在沙發夠長,坐得下一人一尸一亡靈。
一陣鈴聲將我從回憶里拽出。
謝遲接通電話。
他的脆弱像是我的幻想,眨眼褪得干干凈凈。
平日里他的聲線很沉,總給人冷漠的壓迫感。
此刻也不例外。
電話那頭不知說了什麼,他搭在沙發上的手掌緊握成拳。
皮下的青筋躍動,彰顯著主人的情緒。
他冷聲命令:「帶來見我。」
「見誰?」我下意識問。
可惜就一句話,我判斷不了。
我從不自找煩惱,得不到答案就將問題拋到腦后,繼續看我愛的綜藝。
如果從前有人和我說死后還能看電視,我一定覺得對方瘋了。
但我現在確實在這麼做。
謝遲一直沒換臺,我津津有味消耗時間,他毫無前奏開口:「林若。」
「啊?」
我愣了愣。
那不是殺死我的那女孩嗎。
謝遲怎麼突然提起她了?
可惜他說完又閉嘴了。
我繞到他那側,趴在他肩頭吹了口氣,想了想,吐口而出曾經看過的網絡句子:
「我這輩子最討厭兩種人,一種就是說話說到一半的。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