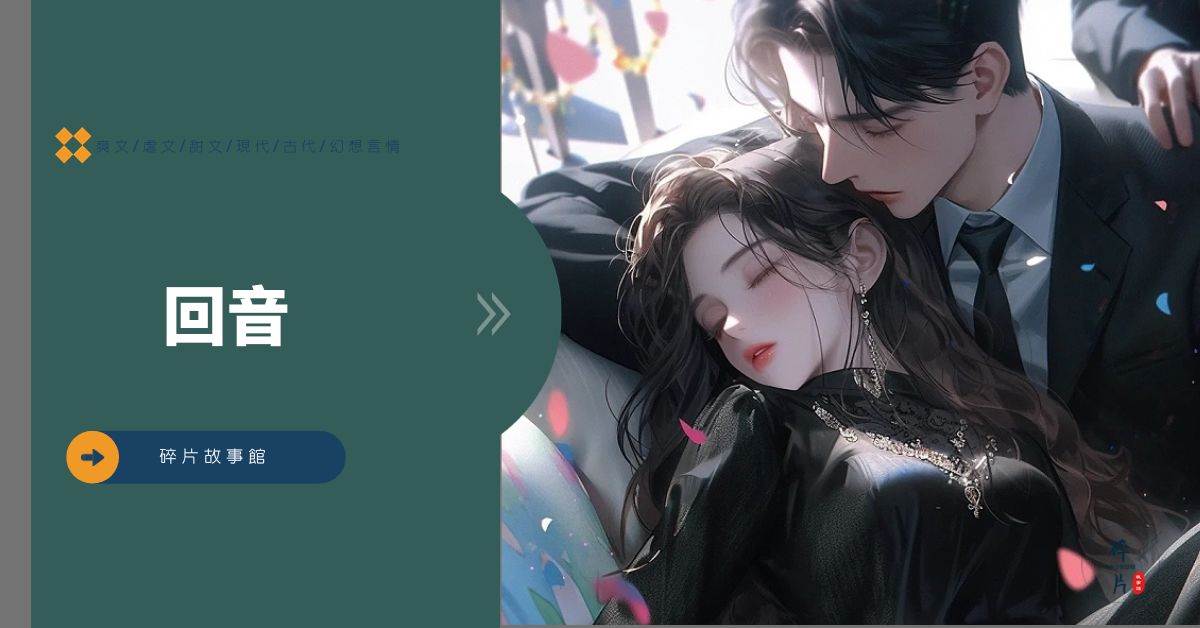《回音.》第1章
我失憶了。他們說我曾為他瘋魔。
我皺了皺眉,仔細打量眼前人的眉眼,心里很是疑惑。
我轉頭去看好友,問道:「裴誕呢?他為何不在?」
好友頓時紅了眼眶。
眼前的男人煞白了臉。
我聽見他顫抖著嗓音問:「裴誕是誰?」
男人眼眸里的情緒在濃烈翻滾。
我摸不著頭腦,但還是禮貌地揚起嘴角,歡快回道:
「裴誕啊,他是我最愛的人。」
1
我失憶了。
睜開眼時,眼前一片白,鼻尖彌漫著消毒水的滋味。
這味道我并不陌生。
從小聞到大。
我不禁在心里嘆口氣,呼吸機里頓時起了霧。
怎麼又進醫院了?
這個破身體。
臉上有些癢,我正欲抬手給自己撓一撓。
卻發現手被人緊緊攥住。
此人手心溫熱,手指修長有力,和我十指緊扣。
我認真摸了摸,眉頭越皺越緊。
這不是裴誕的手。
心里一驚,我連忙縮回手。
但卻被攥得更緊。
我垂眸去看,只能看到一個發頂。
是一個男人,頭發烏黑。
他睡著了。
就在我努力掙開手時,男人也察覺到動靜。
他慢慢睜開眼,睡眼惺忪,眼下一片青黑。
在發現我動手指后,我明顯感覺到他身體變得僵硬。
男人緩緩朝我看來。
真是好俊一張臉。
我感嘆道。
默了默,我瞧得更仔細了。
男人眼里竟閃動著水光。
他神情激動片刻后終于平靜下來。
沒有表情的臉看起來有一點點嚴肅嚇人,臉色冷峻。
「阿阮,我去叫醫生。」他沉聲道,嗓音帶著哽咽。
我迷茫地看著他走遠。
腦子里將所有人都想了個遍。
一無所獲。
不是,這大帥哥誰啊?
2
醫生很快魚貫而入。
ADVERTISEMENT
一大群人圍著我,檢查后悄悄松了口氣。
有人說道:「蕭先生,阮小姐這關算是挺過去了,等腦子里的淤血一散,她就可以恢復記憶。」
男人西裝革履,蒼白的臉稍稍恢復了些微血色。
他轉頭朝我看來,眼睛里有著劫后余生的慶幸。
我眨了眨眼睫,彎了彎唇,算是回應。
醫生出去后,一室寂靜。
男人走得緩慢,但堅定。
他坐到我床邊后,別扭地露出了一個笑。
看得出來,他很少笑,因此表情有些奇怪。
寬闊的肩背微微下彎,他小心握了握我的手,像是對待易碎的瓷瓶。
他低聲喃喃道:「阿阮,還好……」
我不知道還好什麼,他始終沒說下文。
手上傳來的觸感讓我很不自在。
我不認識他,可他明顯認識我。
而且……好像……關系匪淺?
呼吸機已經取下。
我微微動了動唇,但聲音很輕,近乎呢喃。
男人覺察到,立馬站起身,朝我彎下腰。
他身上有濃濃的消毒水味,可見在醫院待了很久。
「阿阮,怎麼了?」他黝黑的眼眸注視著我的眼睛,問道。
極其耐心。
「裴誕……在哪兒?」我努力問道,喉中艱澀。
男人手一頓。
他俊美的臉稍稍側過,正對著我:「什麼?」
那雙明眸閃過一絲不解。
「裴……誕……在哪兒?」
調整呼吸后,我提高音調,口齒清晰一字一頓問道。
眼神執著到近乎偏執。
男人徹底愣住了。
3
裴誕是我繼兄,大我四歲。
我六歲那年,他被他母親帶著進了我家。
那時的他臉上還有嬰兒肥,長相白俊,眉目清潤,看人自帶三分笑。
我很愛纏著他,總是「哥哥、哥哥」叫個不停。
他每一次都會耐著性子認真回應我。
ADVERTISEMENT
十三歲那年,爸爸和沈姨在一個雨夜車禍身亡。
不過幾天,財產便被親戚瓜分殆盡。
我成了一個被踢來踢去的皮球。
至于裴誕,沒有一個人要他。
我過了寄人籬下的生活整整一年。
直到升入高中,要拿學費時,大伯才徹底撕破臉。
是裴誕將我撿回了家。
那年他十八歲。
他溫柔地摸著我的頭,說:「寧寧,哥哥送你讀書。」
那時的我不知道,他已經輟學了一年。
因為要給我湊學費。
他說在本地讀大學。
我信了。
一室一廳的出租屋很敞亮,有一間小小的臥室。
太陽出來時,陽光會落在我柔軟的床鋪上。
裴誕睡在客廳的沙發上,他睡著后,清俊的眉眼會輕輕蹙起。
仿佛在夢里也有很多無可奈何的事。
冬天,天氣很冷,出租屋冷得讓人恨不得裹緊幾床被子。
只有我的臥室,有一臺空調。
我周末回家時,臥室總是暖乎乎的。
可是裴誕要睡在冷冰冰的客廳。
我提議一起睡。
但他不同意。
那是我們爆發的最大一次爭吵,或者只是我單方面的哭鬧。
「哥哥,沒關系的,真的沒關系的。」我哽咽心疼道。
哥哥笑得溫柔無奈,他抬起手輕輕擦去我的眼淚。
然后堅定地搖了搖頭。
最后是我賴在沙發不走,大有他不同意我也睡在客廳的架勢,才讓他踏進了那間臥室。
我睡在床上,他在地下打地鋪。
那是他的底線。
空調的暖氣在彌漫。
我在厚重柔軟的被窩里熱出了汗。
冰冷的地板,單薄的床單,裴誕小心地翻身,生怕吵醒我。
我側身睡在床沿,借著清冷的月光打量裴誕漂亮的臉。
從他輕皺的眉頭,到高挺的鼻梁,然后是薄薄的嘴唇。
裴誕高一時就已在學校帥名遠揚。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