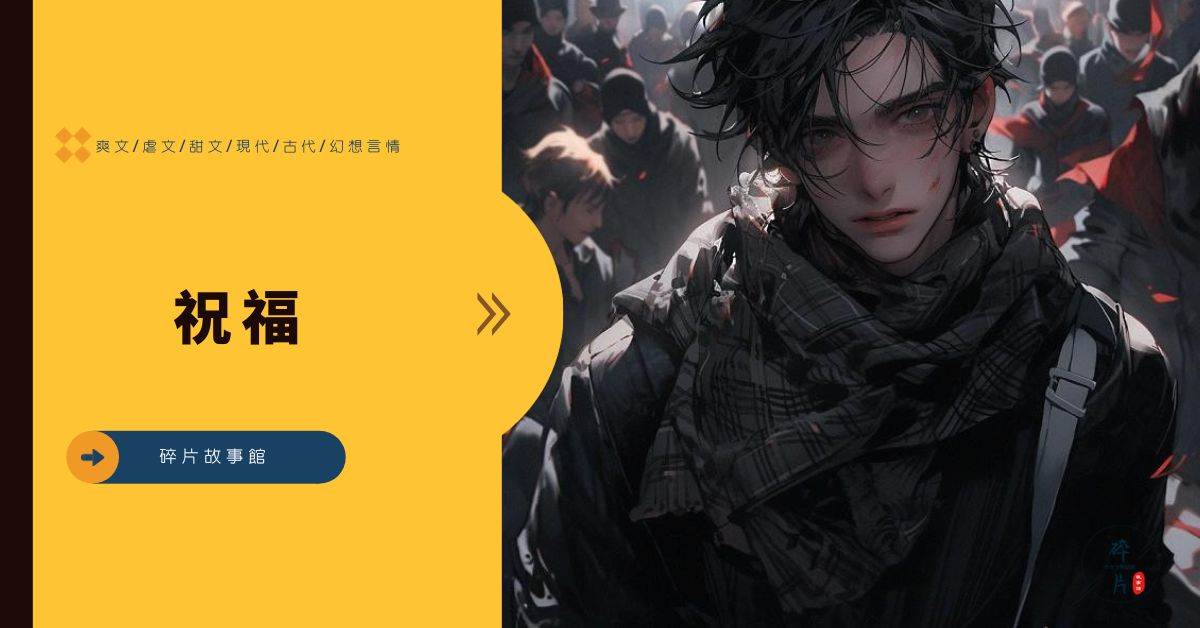《祝福》第8章
不同于三年前,這次離家我沒有帶走任何東西。最后也是阿源替我拿了錄取通知書。
我把我的名字賀文希給了阿源,阿源把他的大名陳淵給了我。
我填的志愿在外省,不會再和同學有交集;他成年了也可以離開孤兒院,再也不用回去。
為了盡可能減少對他的影響,我用燒傷和刀傷毀壞相貌。從此賀文希只能是他一個人。
之后的幾年,我們保持著微弱的聯系。我知道他帶著母親過得很好,他上了我填的那所醫科大學,成為了一名醫生,定居在一個宜居城市,下一步就是娶妻生子,共享天倫。未來的發展都會如母親所愿。
我也能了無牽掛地走向我的命運。
這種感覺很奇妙,不是嗎?就好像把兩個平行時空并到了一起。
我翻的不是案,而是一個兒子的人生。
讓那位母親擁有一個值得她托付終身的兒子,是我對她最深的祝福。
12
「回到之前的問題,為什麼在法庭上我沒有供述真正的動機。」陳淵解釋道,「因為被性侵的是賀文希,我陳淵和周鴻興無冤無仇,自然只能隨便找個理由糊弄過去,否則就和履歷矛盾了。」
「反正都是要死刑的,動機也不重要,一年前我就做好了赴死的準備。誰知道賀文希高價請了經驗豐富的律師給我做辯護,爭取了死緩。
「死緩也挺好,平時通通信,還可以了解母親的近況,只要不被母親發現就行。我對人世唯一的貪戀也就這點東西,要不是前段時間被他老婆發現,我也不會出此下策。
ADVERTISEMENT
怪只怪馬鳴倒霉了。」
故事講完,我仍然沒回過神。
陳淵看了看時間。
「時間差不多了,我該上路了。」他從容起身。
「這是真的嗎?」我連忙發問,「你剛才講的都是真的嗎?」
「把陳淵帶出來!」門外的同事高聲喊,「到點了,準備驗明正身!」
陳淵說:「是真是假已經不重要了。為什麼臨刑前才說,就是因為現在不重要了。臨死前隨便說說,有什麼要緊的。」
兩名法警把陳淵帶走了。
我呆坐片刻,追出去。
昏暗的走廊盡頭,天還蒙蒙亮。腳鐐沉重遲緩的當啷聲越來越遠。
「等一下——」我喊了一聲,正要追。
后面一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小陸,你干嘛呢?」
我一驚,回頭看是我的前輩。等會兒負責驗明正身的就是他。
我趕緊拉住前輩,語無倫次地把陳淵的事復述一遍,太過著急, 以致前言不搭后語。
前輩沉默片刻,兩句話就讓我噤了聲:「罪是他犯的嗎?兩個人是他殺的嗎?」
「是的。」前輩自問自答,「我不知道他以前叫什麼,他現在叫陳淵,檔案上也是陳淵。不管他是主動跟人交換了名字,還是高考被冒名頂替了, 管他什麼原因,罪確實是他犯的。那麼驗明正身會有問題嗎?不會。對結果有什麼影響嗎?沒有。他在編故事, 不要多想了,這麼離奇的故事你也信,小陸, 你還是太年輕。走吧。」
聽完前輩的話,我漸漸冷靜下來, 搖了搖頭, 緩步跟上去。
驗明正身,交付執行,一切都按程序進行。
一大早,太陽還沒升起, 整個刑場籠罩在幽藍晨光中。山風裹挾著霧氣, 又濕又冷。
我打了個寒顫,才驚覺我跟上了刑場, 這是我第一次來到刑場。
ADVERTISEMENT
而眼前這一幕和陳淵描述的何其相似。
陳淵講的故事無論是真是假,都不會影響他的結局。
——可他的故事,到底是真還是假?
陳淵走上那片空闊的草地,靜立片刻, 就跪下了。
從判決書下來到現在,他一直都很冷靜,無牽無掛,無欲無求。
槍上膛的那一刻,他一個激靈,猛然抬頭,看向遠處。
我也頓時想起什麼,順著他的目光看去。
一眼便看見,西山第二機械廠最西邊的宿舍樓。因為廢棄太久,墻體布滿裂縫, 窗戶都是破的。
樹叢掩映間, 某一扇窗外突兀地裝了個花架子。
上面有個紅陶花盆,雜草叢生。
恍然間, 我看見一個女人探出身子, 低著頭澆水的身影。
心跳猛然漏掉一拍,我匆忙收回目光,張皇地看向陳淵。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槍口對準他的后腦——
他的瞳孔驟然散大,瀕死的目光緊緊盯著遠方的窗臺,嘴唇發著抖、呼著氣, 只有出氣, 沒有進氣——
法警提醒:「嘴張大!」
他跪在地上,仰著頭,竭盡全力張大嘴, 哭嚎道:「媽媽!——媽媽!——」
槍聲響起,被驚起的鳥都寥寥無幾。山野重歸平靜。
我想那個答案,已經不言而喻了。
-完-
核熔爐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