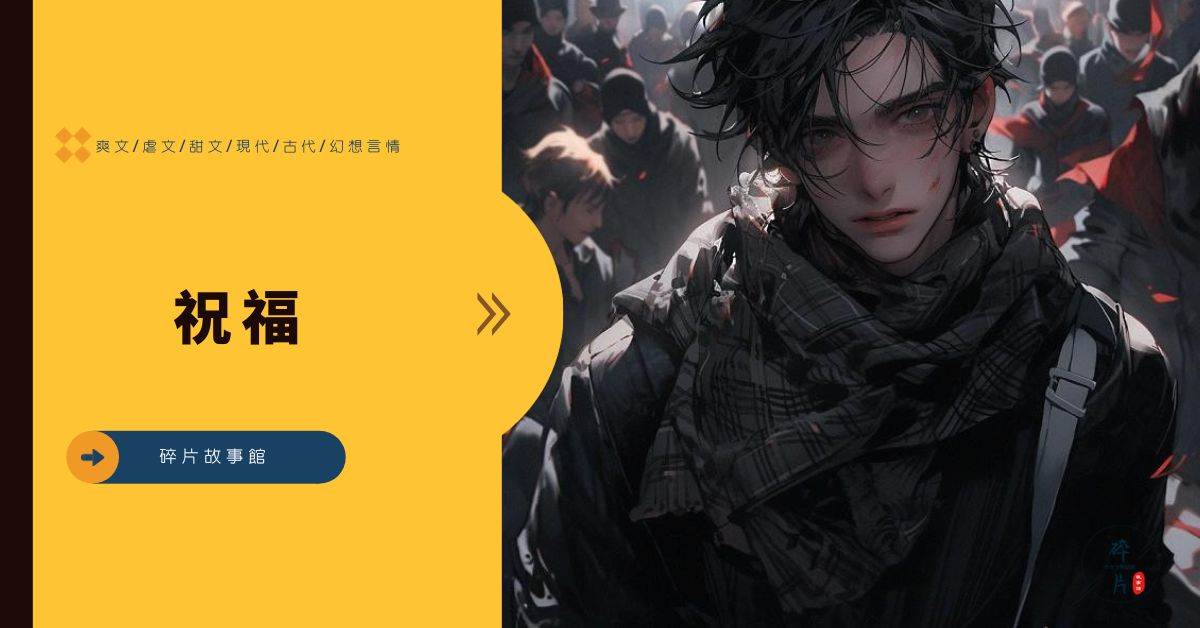《祝福》第4章
很多女人就是這麼柔弱,明明也能自食其力,但內心依然渴望有所依靠。
她就剩一個兒子了,她在我身上看見了虛妄的未來,因而把全部希望托付在我身上。她指望我能像大多數普通人一樣,讀書工作、結婚生子,指望以后能依靠我。
她沒做錯什麼,她只是個正常的母親。
但我不是正常的孩子。
我無法回應母親的期待,我在她身邊感覺到壓抑和痛苦。
讀書工作、結婚生子,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唯一渴望的只有犯罪,那是我必然要走的路。
你可能奇怪,為什麼我對未來的犯罪道路如此篤定。
因為這是我嘗試過自救后的結果。
在診所的光陰其實不算虛度,我遍閱楊醫生的心理學藏書,才發現得救之道,就在其中。
童年的創傷經歷會產生蝴蝶效應,對人的一生都產生重要影響。這就是童年陰影的可怕之處。
我從一個好孩子突變成壞孩子,其實是有跡可循的。
之前我刻意回避那段經歷,以至于痛苦了許多年。
自學心理學后,我逐漸明白了,如果童年陰影造成的心結不打開,我就會一直痛苦下去,永遠無法解脫。
小學二年級,我將同學鎖在廢棄的儲物間里,旁觀所有人著急找尋。但我和那個同學沒有過結,傷害我的是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叫周鴻興。
周鴻興對我——一個七八歲的男孩——實施了性侵。
那時年紀小,很多東西不明白,但是親眼看見一個和善的大人忽然變得面目猙獰是真實的,親身感受到的恐懼與疼痛也是真實的。
ADVERTISEMENT
事后我很害怕,把這事告訴父親,希望他能幫我討回公道。但父親瞻前顧后,最后只叫我別再去同學家。
父親尚且不敢對抗,我就更不敢了。我又難以排解痛苦,就只好報復周鴻興的兒子。
普通的報復讓人不痛不癢。我僅僅只是把他兒子關在儲物間里,他就又性侵了我一次,警告我不準再動他兒子。
一直以來,周鴻興都是個溫厚和善的好人,他對誰都好,對誰都是一副笑面孔。
他第一次見我就笑著說:「這孩子長得真討人喜歡。」給我買了很多好吃的。
卻偏偏到最后,把最可怕的嘴臉都給了我。
沒人會相信一個孩子對一個好人的指控,我父親都不相信。
后來,我沒再跟人提這件事,但我逐漸變得敏感陰郁,睚眥必報。
往往只是一些無足輕重的小事,我便立刻展開猛烈報復。每一次報復都像是彌補第一次無法報復的遺憾。
可是都如同隔靴搔癢,始終難解心頭之恨。
我逐漸意識到,周鴻興才是我的心結所在。沒有人能救我,除了我自己。
我必須殺了他。
從十年前開始,我就計劃著要殺周鴻興。曾經我年紀小,面對他的侵犯沒有任何反抗之力。現在我長大了,他老了,我弄死他就像捏死一只蒼蠅。
你說我讓周鴻興幸福的一家蒙上陰影,你怎麼不說他毀了我一輩子呢?
殺了他,我才能得到解脫。
這就是我殺周鴻興的真正原因。
8
陳淵的敘述過于冷靜,開口閉口說恨,語氣卻很平淡。
「等一下,」我出聲打斷他,「你之前說的是你和周鴻興在路上撞到,產生口角,你懷恨在心,尾隨他并將他殺害。
ADVERTISEMENT
結果你現在說你們不是偶然碰上,你早就計劃要殺了他?」
「我殺人拋尸時有人目擊,但是我和周鴻興產生口角,這里有目擊證人嗎?沒有。」陳淵笑道,「所以產生口角什麼的,我說說就行了,周鴻興又沒機會說。」
「所以你殺周鴻興的真正動機,其實是為童年被性侵的事報仇。」我了然道,「這樣的話,你打死馬鳴似乎也合理了。同樣不是因為產生口角,而是因為馬鳴猥褻幼童,喚起你童年痛苦的回憶,所以你打死了他。」
陳淵說:「是的。」
我進而想到,陳淵入獄以來只聯系過一個同性友人,讓我們疑心他有同性戀傾向,這也變得合理了。
因為確實有不少后天同性戀者,幼年時期有過被同性猥褻的經歷,從而強行扭轉了性取向。
可是,跳出這段故事,仔細想一想——
放在這樣的情景下,有西山刑場,有同性友人,有同質的殺人動機,有兩名受害者,有一個死刑犯。一切都串聯起來,顯得過于合理了。
合理得就像一部基于現實情形編造的、合乎所有邏輯的小說,而他是其中殉道的主角。
「你講的故事確實讓人痛心。但是,不要再編故事了。」我有點失去耐心,「我問你,你和周鴻興產生口角確實沒有證人,那你童年被周鴻興性侵有證據嗎?周鴻興的兒子對你恨之入骨,你說他是你的小學同學,但實際上他完全不認識你。當然你也可以解釋說,長大后長相變化大,但名字總該有印象吧?」
陳淵不以為然,「我小學同學的名字基本都不記得了……」
我打斷他,「我理解你們的心理。有些犯人也和你一樣,閑得沒事不好好改造,光想著編故事,捏造事實抹黑受害者,給自己的人生添油加醋,把自己犯的罪合理化,好像全世界都背叛了你。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