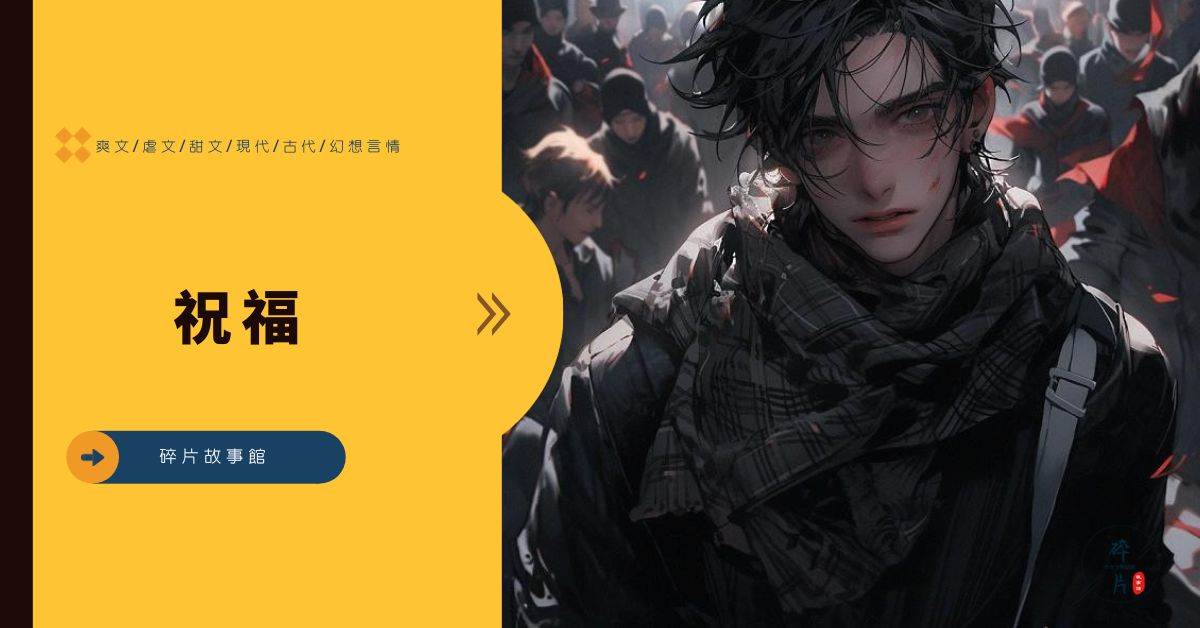《祝福》第2章
等到槍上膛的那一刻,他們才忽然清醒過來,有的拼命求饒,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掙扎著想跑,被嚇到大小便失禁的也不少見,但最后總會被乖乖制伏。
然后他們跪在地上,在法警的示意下張大嘴巴,迎接身后的審判。槍聲一響,被驚起的鳥都寥寥無幾,山野重歸平靜。
等待行刑的過程是煎熬的,真正到了點,也就是一瞬間的事。
可是死了就是真的死了,趴在地上動也不動。之前不管他們是哭是笑,是跑是鬧,最后都是這樣一動不動趴在地上,變成一具尸體。
他們的神情都平靜安詳。因為張大了嘴巴,子彈從腦后穿進,從嘴里穿出,面容就不會受到太大破壞,以便料理后事。
那年我十五歲,每天早上起來都要看一眼刑場,既害怕,又想看,看完渾身發抖,起雞皮疙瘩,頭腦里嗡嗡作響,好像那一槍是打進我腦袋里的。
我幾乎每天都要挨這麼一槍,然后去上學。
陸醫生,這樣的經歷是不是還挺特別的?
4
聽完陳淵的講述,我說:「確實特別,你所說的西山第二機械廠也在附近,已經廢棄多年了。但我不能確定這就是你的真實經歷,故事本身也有些奇怪。」
他問:「哪里奇怪?」
「你一開始說,是你母親帶你搬到這里的,所以你母親是在西山第二機械廠工作,對嗎?我不相信有哪個母親會放任自己的孩子直面死刑現場,難道她對此一無所知?」
「不,她知道。」
5
陳淵的講述(2)——
我每天都會窺視刑場。這事母親知道,這正是她的目的。
實際上,不是因為母親找了機械廠的工作,我們才不得不搬到這地方。
ADVERTISEMENT
因果關系錯了。
母親是因為知道這里有刑場,想搬過來,才選擇來這里工作的。
機械廠宿舍,已經是我們第三個家了。
我幼年時聰明乖巧,人見人愛,是父母的驕傲。
可是從小學二年級開始,我的性格逐漸變得陰暗起來。
我開始經常欺負同學。最開始還只是將同學鎖在廢棄的儲物間里,旁觀所有人著急找尋;到了五年級,就直接把人打得腦震蕩進醫院了。
父母無數次道歉賠罪,賠了很多錢。家長老師輪番教育,但我就是改不了。
母親哭了一夜又一夜,說你以前多乖啊,為什麼會變成這樣,是爸爸媽媽做錯什麼了嗎?
父親每次被老師找,回來都會拿皮帶狠狠抽我,再讓我罰站一整夜。最后一次他抽得尤其兇狠,抽得我蜷縮在地上動彈不得。
但是某一刻對上我的眼神,他就停手了。他忽然覺得害怕,說遲早有一天,我會殺了他。
不久后,父親離開了,再也沒回來。
五年級時,我被學校勸退。因為臭名遠揚,附近也沒有別的學校敢收。
母親沒辦法,只好帶我搬離那個地區。
母親知道孟母三遷的道理,帶我搬到城里一所大學附近,指望我受到文明的熏陶。
到了新學校,老師們都喜歡我,因為我學習成績很好,彬彬有禮又聽話。母親也以為我終于變好了,松了一口氣。
但這都是我善于偽裝的結果。
好了沒兩年,上了初一,我就伙同人販子差點把隔壁女大學生拐賣了。
女大學生的男友不肯罷休,跑到我的學校鬧。老師喊我去對質,我口袋里藏了把匕首去,差點釀成大禍。
ADVERTISEMENT
母親跪在校長辦公室里,祈求校長網開一面。
校長態度堅決,他說我無底線無家教,這種品行惡劣的小孩遲早會犯事,學校承擔不起后果,叫母親好自為之。
然后我就又被勸退了。
母親生了一場大病,病愈后仿佛清醒很多。
她帶著我再次搬家,搬到這里。
西山第二機械廠最西邊的宿舍樓,因為緊挨著西山刑場,其他工人家庭都避之不及。
誰不幸擁有這樣一套「觀景房」,都會用木板把那邊的窗戶封起來,永久關閉,以免不小心看到不該看的。
母親也采取了類似的措施,但她用的是報紙,既封了窗戶又不影響采光。
而報紙糊的窗戶,還是可以打開的。
她甚至在我房間的窗外做了個花架子,搬了只紅陶盆上去,養了盆蘭花。她每天早上都去澆水或者修剪,低著頭垂著眼,不敢往遠處看。
但卻為了通風把窗虛掩著,以便我起床就能直接觀摩死刑現場。
我明白母親的用心。她知道正向感化行不通,就選擇了反向教化,讓我看看壞人是怎麼被槍斃的,希望我能感同身受、有所畏懼,以此來約束自己,成為一個好人。
最開始,我是真的被槍決死刑震懾住了,我又變成了一個好好學習的乖孩子。
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內心很痛苦,我強忍著行惡的欲望,甚至痛苦得開始自殘。
我的手臂上、腿上都是自殘的傷痕,我的精神也搖搖欲墜。
要想克制自己不去犯罪,也不是件易事啊。
陸醫生,你看。
6
陳淵戴著手銬,不方便卷袖子,于是他低頭咬著袖子往上拉,給我看他手臂上的舊傷疤。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