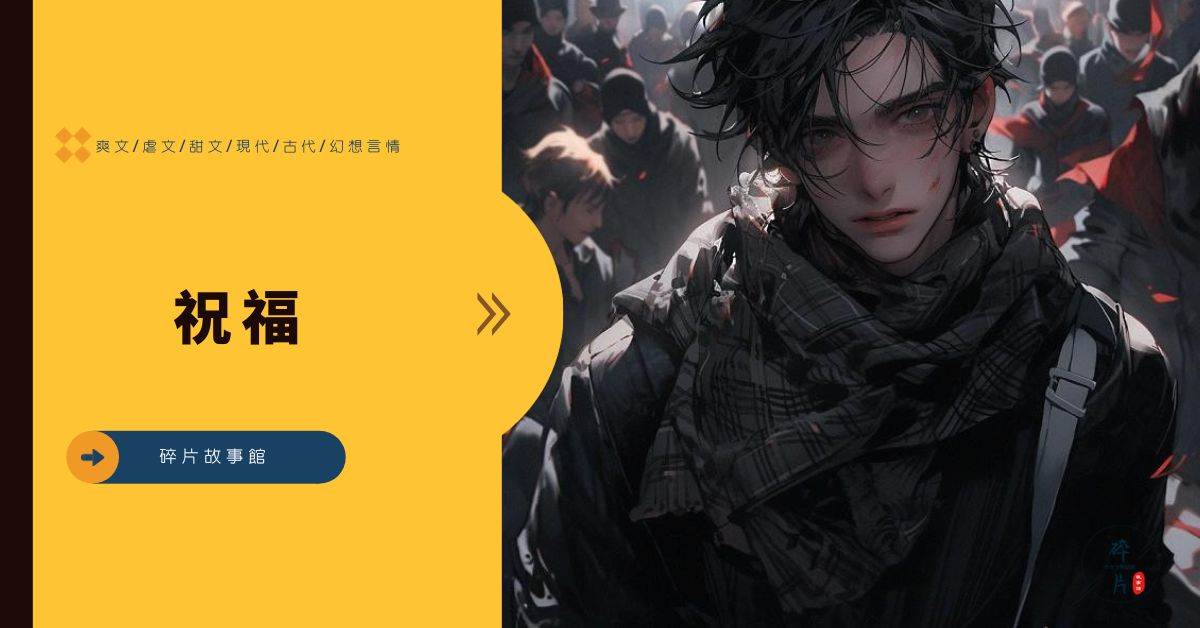《祝福》第1章
距離行刑還有兩個小時,我走進監舍,給那名死刑犯做臨刑前的心理疏導。
死刑犯說:「馬上我就要被槍斃了,一切都將塵埃落定,這樣的結局可真沒意思。但我還想再掙扎一下——怎樣才能扭轉這種無聊的結局呢?」
「不如給你講個故事吧,陸醫生?」
他意味不明的笑容令我不寒而栗。最后兩小時,難道他還想翻案不成?
1
2005 年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西南山區一所男子監獄的教改科,成為了一名心理輔導老師。日常工作就是給服刑人員進行心理教育,幫助他們矯治不良心理,以便更好地參與改造。
有一個叫陳淵的犯人,原本不是我的重點關注對象。他因故意殺人罪被判死緩,已經服刑一年多了;表現中規中矩,算不上積極,但也都服從命令,從未與人起沖突;平日里寡言少語,在一眾情況復雜的犯人中沒什麼存在感。
只要再安分幾個月,陳淵就能度過死緩考驗期,減為無期徒刑。
可是變故發生了。
前段時間,陳淵忽然暴起攻擊他的舍友,單方面的施暴,拳拳都往致命處去,十幾秒就把人打得重傷不治。值班民警都未及反應。
一年來的乖巧表現,讓人差點忘了陳淵是個殺人分尸的惡魔,只因辯護人討巧才能獲得緩期兩年的恩典。
如今陳淵還是迎來了他應有的結局。死緩考驗期故意犯罪,情節惡劣,自然不必再緩,死刑成了板上釘釘的事。
判決書下來后,我們提前一天通知了犯人。陳淵得知自己人生的最后 24 小時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ADVERTISEMENT
明天,他可以和親屬會面,洗個痛快澡,吃一頓好飯,接受心理疏導,然后驗明正身,交付執行。
陳淵露出一個奇怪的表情,沒有說話。
我問:「你有什麼疑問嗎?」
「沒有。」
2
第二天,陳淵被押赴死刑監獄,我作為心理輔導老師也需陪同前往。
臨刑前可以安排家屬見面,但陳淵是孤兒,沒有家屬。此前從未有人探望,此刻也無人與他告別。
陳淵唯一聯系過的只有一個男性朋友,名叫賀文希。他們每隔兩個月通一次信。
服刑人員的信件必須經過審閱,確認內容正常才能傳達。陳淵寫信就是問候對方及家人近況如何,對方再詳細作答。信的內容沒什麼問題,但字里行間隱隱有些古怪。
收發室的同事幾經斟酌,發現了其中微妙的親密感,似乎不像普通朋友。他們由此得出了驚世駭俗的結論。
可這個親密的朋友賀文希,也從未在探視室出現過。
上一封回信比較特殊,是賀文希的妻子寫來的。她發現了端倪,來信質問陳淵是誰。
這才知道,賀文希不久前結婚了。我們推測這就是陳淵忽然發瘋的原因。
現在陳淵墜墜地戴著手銬腳鐐,靠口述給賀文希寫了最后一封信,依然是普通的問候,多添了一句「不必回信」。
距離行刑還有兩個小時,我去給陳淵做心理疏導。
陳淵的長相算得上文質彬彬,像個讀書人,但臉上的刀疤和燒傷痕跡平添了幾分陰狠。
他端坐在監舍中央,看起來異常冷靜。
再硬氣的犯人到了這個環節,往往都會追悔痛哭,而陳淵給我的感覺好像是他根本不會死。
ADVERTISEMENT
我說:「陳淵,還剩兩個小時了,你要做好心理準備,還有什麼想說的嗎?」
陳淵說:「我都要死了,還關心我的心理健康啊。多此一舉了。」
「這是必要的人道主義關懷。」但我感覺他確實不需要。
「陸醫生,聽說你是犯罪心理學的高材生,結果現在就干這個,是不是有點屈才了?」
我一時無言以對。
陳淵繼續說:「我也學過心理學,真正的心理學可不會像這樣沒用。」
我接過話茬:「那麼你學的心理學,用處在哪里?」
「想知道嗎?」他頓了頓,意味深長地說,「馬上我就要被槍斃了,一切都將塵埃落定,這樣的結局可真沒意思。但我還想再掙扎一下——怎樣才能扭轉這種無聊的結局呢?」
「難道你還想翻案不成?」
「不如給你講個故事吧,陸醫生?」
我點點頭,「這是你的權利,我洗耳恭聽。不過時間不多了。」
3
陳淵的講述(1)——
外面就是西山刑場,我對這地方很熟悉,因為原先我家就在這附近。現在回到這里就像回家一樣,似乎也算是一種「視死如歸」。
1995 年,我 15 歲,念初二。母親帶我搬到這里,西山縣第二機械廠單位宿舍。現在那一片已經廢棄了。
我們那棟宿舍樓在最后一排,緊挨著西山刑場,之間攔了一道鐵絲網,種了一排雪松。
但是從房間窗戶往外看,還是能從樹叢掩映間窺得刑場景象。
每天早上六點,我起床后都會拿望遠鏡觀摩槍決現場。
一大早,太陽還在山坡那一頭,整個刑場還籠罩在幽藍晨光中,死刑犯就被押赴刑場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只要站在那片土地上,無一例外都是耷拉著肩膀,一臉灰敗死氣,好像神魂已經脫離。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