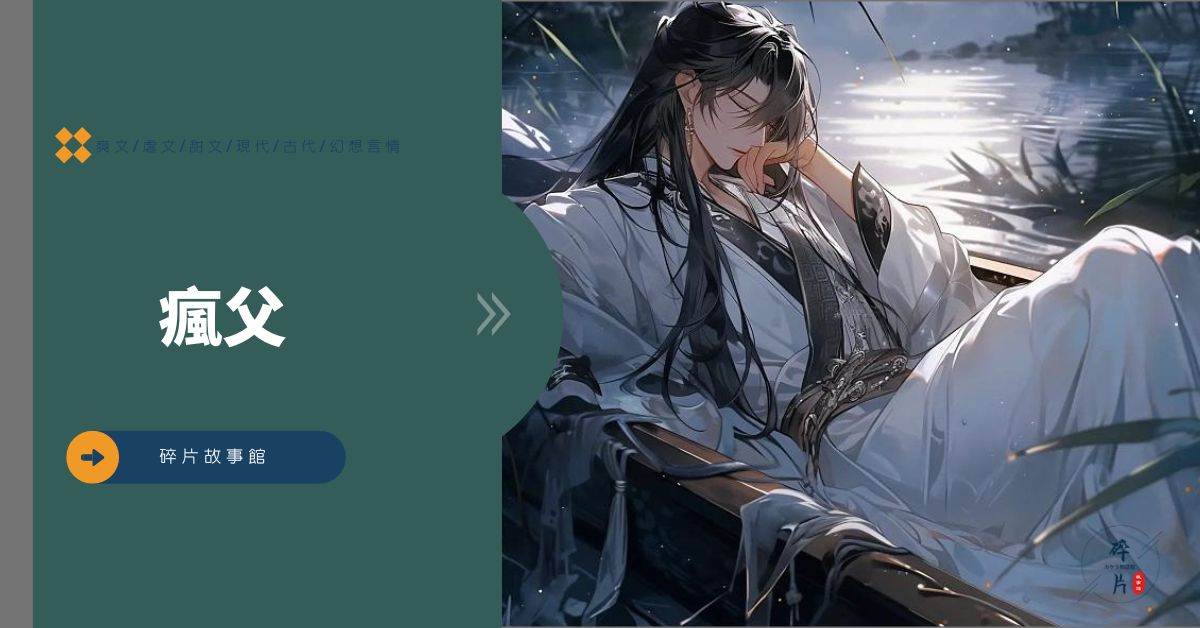《瘋父》第5章
元鶴冷冷說道:「下一個便是你了。」
僵持間,宮人來報。
說司南禮找著了。
我站起來,猛地轉過身去,揪著人問:「尸身如何了?」
「不,不是尸身,還活著,昨夜起火時司南禮根本不在宅中,因而沒有葬身火海。」
我松開手。
心情激蕩得難以言明。
這時,遠遠地傳來左相的聲音:「崔永這逆徒,早就離心了,他可是連夜去轉移了司南禮。」
我怔怔地看向左相。
父親司南禮就在他的身后。
11
我頭一回在父親的臉上看到那樣沉靜清明的眼神。
好像從來沒有瘋癲過一樣。
我想起來,從前我待在冷宮時,大約是八九歲的時候,已經發現父親清醒的時間比我更小的時候要多些了。
他終于徹底清醒過來了嗎?
父親跪下來,朝元鶴磕頭:「是臣將裴淼下落告知公主,才致公主帶人去沖撞了先皇,一切歸因在臣,臣愿替公主領罰。」
我心里發急,顧不得與元鶴的嫌隙,連聲求饒:「太子殿下,司家舉族本就是無辜受害,不能再殺了。」
元鶴居高臨下地睨著我,良久才說:「將司南禮打入地牢,至于公主……」
左相提醒道:「太子,此時不宜處置公主,若將事情鬧大了去,反讓人去深究陳年往事了。況且,她是你親姐姐。」
元鶴露出不屑的神情。
父親仍伏低著身子,沉聲道:「臣領罰。」
他被帶走時,我拖著他問:「你領什麼罪,不是說過我不是你的親女兒嗎?你替我領什麼罪……」
父親掰開我的手,垂頭看了我一眼,笑了笑,什麼也沒說。
12
元鶴把公主殿的人全撤了。
兜轉間,我又似回到了冷宮。
ADVERTISEMENT
直至半夜,飄來一陣血腥氣。
血跡斑斑的崔永跌撞地走進來,他被打得半死。
沒走幾步,倒地不起。
身上全是鞭傷。
我用冷水浸濕毛巾,左一塊又一塊地給他敷上緩解痛楚。
崔永卻說:「公主,不用折騰了。」
我扶起崔永,讓他枕著我,這樣會舒服些。
我撥開他額前被汗水浸濕的發絲,看著他那雙墨玉般的眸子,輕聲問:「你明知道左相要縱火殺人,為何要暗自忤逆他,提前去藏人?」
崔永眼神渙散,話也說得很慢。
他一點點地說:「司南禮還是翰林時,我全家獲罪,成年子女流放,年幼著沒入官奴,那時我七八歲。」
「翰林心慈,念我年幼,常加照拂,公公打我板子,他便私下請來太醫為我保住性命。」
「還有,他請我吃的茉莉花糕,是我這麼多年來吃過味道最好的糕點。」
「后來,我念他的好處,就請命過來伺候公主。」
我道:「他是心慈,明知我并非親生的……」
崔永雙目一睜,急促地問:「公主說什麼?什麼并非親生的,您是翰林與先皇的親女兒,這點絕作不了假。」
「爹說過,他親眼見著先皇長女是死胎。」
「是,是有一個死胎,」崔永說,「本為雙生胎,先生出來的夭折了,公主您是后生的。」
外面一聲驚雷,須臾間大雨傾盆。
「崔永,我明天就去告訴他。」
「好。」崔永微微笑了笑。
他的手從腰間滑落下來。
我去抓,發現脈息已斷。
崔永,走了。
我冒雨去地牢。
他們攔我。
我就抽出侍衛的劍,胡亂砍一通,都只好給我讓路。
我在地牢里一路跑,迫不及待地要見父親。
我有很多話要和他說。
ADVERTISEMENT
我在盡頭找到父親了。
他坐在角落里,頭低垂著,一動不動。
身上有數條毒蛇橫縱,噬咬。
父親在我來之前,就已經毒發身亡。
元鶴之心,賽過毒蛇千百倍。
我捅傷了侍衛,又把劍架在別的侍衛身上,逼迫下,得到了一只裝滿毒蛇的簍子。
元鶴此時正在靈堂里禱告。
我便去靈堂,倒了一地的毒蛇。
頃刻間,這里混亂不堪,尖叫、祭品倒地的破碎聲揉雜著,靈堂的寧靜肅穆頓時變得四分五裂。
如同我的處境一般。
13
元鶴的左腿被咬了一口,但不致死,昏迷了過去。
左相趕來時,我已經劫持了裴淼。
當看見鋒利的刀刃頂在裴淼的頸項時,他腳步一滯。
左相屏退了所有人。
他伸出手,示意我冷靜:「元謠,我可以放你離開。」
「你很緊張裴淼嗎?」我問,「你若真的緊張,怎麼會毒啞她的嗓子廢了她的雙手?」
左相臉色一沉,道:「我明明是在保護她。只要她什麼都不說,余生都能安安穩穩的,可偏偏那天她逃出去,還碰上了司南禮。」
「我瞧裴淼是生不如死啊,」我冷冷地說,「你打著救她的旗號,泄露軍情,栽贓同僚,害得她外戚俱亡,一人不剩。」
左相輕描淡寫地說:「這不是我也沒想到鈺婉會動那麼大的怒火。」
我忍不住笑出聲來:「沒想到?」
左相回憶道:「鈺婉十三歲起就戀慕司南禮,誰能想到事發時,會絕情成那樣。」
「她是皇帝!叛國當前,自然以大局為重,倒是你,毫無理由讓司南禮擔了判國之罪。」
「不是毫無理由,」左相看了一眼裴淼,「鈺婉只知道裴淼與司南禮是青梅竹馬,卻不曾知道我才是真正喜歡裴淼的人。
」
他停頓一下,「裴淼去和親時,還是鈺婉的父皇在位。可惜沒多久就駕崩了,我只好遷怒鈺婉,鈺婉所在意的,我也要摧毀。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