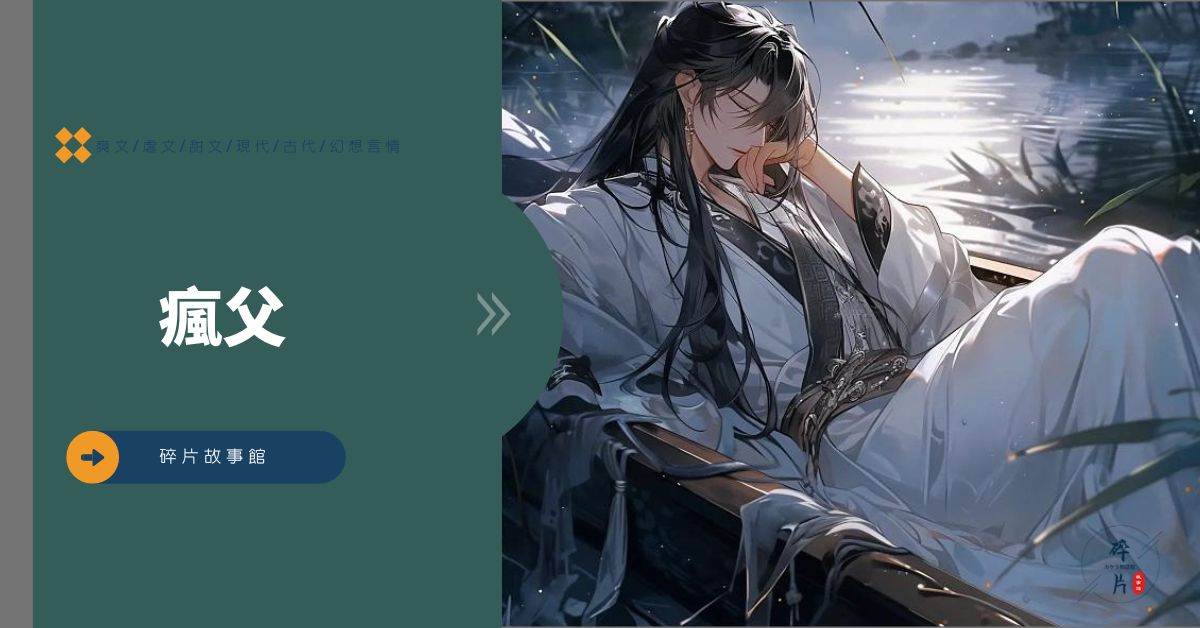《瘋父》第4章
我意識到自己失態,訕訕地說:「沒什麼,我走了,以后再來看你。」
我轉過身去,步伐沉重,全然失了來時的雀躍。
父親這時忽然拉住我,期待地問:「表妹,我上次翻墻出去時,是不是碰上過你一回?你那時拼命扯住我是要說些什麼啊?你支吾了好久沒說出來。」
我驀地滯住腳步。
送去和親并且已經死在異邦的裴淼,何以讓父親上一回「見過」。
我回過頭,對父親說:「我那時就是想問,你過得好不好?」
「嗯,」父親重重地點頭,「你剛看見了,鈺婉為了不讓我難過,還給了我一個假女兒,騙我這就是我的孩子,若不是我當年親眼看見,還真被蒙過去了。我同你說,謠謠從小就可愛乖巧,我很喜歡她。」
我吸了吸鼻子,輕聲道:「好,我知道。」
臨走時,我問了他最后一個問題。
崔永一直在門前候著。
我對崔永說:「你帶我去找一個人。」
崔永問:「是什麼人?」
我還未說出口,他便接了句:「崔永遵命。」
9
父親說,裴淼那日什麼也沒說出口。
只是往他手里塞紙條。
紙條上全是用血寫成的字,血跡深深淺淺,貌似寫時匆忙又潦草。
我循著上面的地址找到了裴淼。
有人在看守著她。
被崔永收拾了。
我帶著裴淼,一路趕回宮。
裴淼一路無言。
她竟是啞了,嗓子里只能發出嘶啞的咿呀聲。
夜色已深,我帶人徑直闖進了陛下的寢殿。
陛下有些生氣,開口讓人將我逐出去。
我撲通一聲跪下來:「母親。」
陛下依舊冷冷的,但總算是讓其余人先退下了。
裴淼原先正跪著,頭垂到地上,此刻才敢慢慢抬起來。
ADVERTISEMENT
陛下見到她時,瞳孔猛張。
「裴淼?」陛下脫口而出,話音一落,她匆忙走過來將人扶起,「你還活著。」
裴淼眼睛里蘊滿了淚水,她張著嘴巴,要說話,卻依舊只能發出破碎的音節。
我說:「陛下,她說不了話。」
陛下立刻說:「拿筆來。」
可是裴淼剛拿起筆,手就抖得厲害,勉強拿住了,卻無力寫字。
陛下問:「是誰廢了你的嗓子和手?」
她一頓,露出忐忑的神情:「不會是司南禮吧?」
裴淼更著急了,拼命地搖頭。
陛下扶著裴淼的肩膀,使她鎮定下來,再問:「當年起戰時,究竟是不是司南禮在你身上用了假死的法子,然后將你救了出來?」
裴淼依舊搖頭。
陛下的額頭滲出冷汗,胸口微微起伏著,隔了好一會才問出第三個問題:「但軍情,確是司南禮泄露的對嗎?」
幾顆淚珠唰地從裴淼的眼眶里滾落下來,她用盡全身力氣,從嗓子里嘶喊出了一個喑啞的「不」。
瞬間,陛下跌坐在地上。
她捂著心口,大口大口地吸氣,好像隨時要窒息過去。
陛下在慌亂中,目光倏地定在我身上,她凝望著我,眼里翻涌著極致濃郁的情緒。
突然,她瘋了一般地撲向我,把我緊緊摟在懷里,一聲聲地喊謠謠。
每一聲,都絕望至極。
陛下不恨父親了。
自然也不再恨我。
我從三歲時開始期盼的母女情深,實現在十三年后。
可我卻半分都高興不起來。
我像根木頭一樣,豎在陛下懷里,似乎下一刻就要從中間碎開。
陛下終于察覺到了我的冷若冰霜。
她松開手,哭著笑著說你永遠都不會原諒我的。
ADVERTISEMENT
我不發一言。
陛下突然把宮人召進來,聲嘶力竭道:「召左相!不,別讓他來,遣人去接司南禮!」
宮人跌跌撞撞地跑進來:「不好了,陛下,司府突逢大火,燒了一個多時辰,如今總算撲滅了,可里頭的人卻……已成灰燼。」
陛下猛地吐出一口血。
昏暗的燭光下,依舊紅得耀眼。
我呆滯地走出去,腿腳有些發軟,崔永也不見了,沒人扶著,后來摔了一跤。
靜坐至天明時,又傳來一個噩耗。
崔永回來告訴我,陛下去了。
在夜間突發心悸,心悸而亡。
父親司南禮,母親鈺婉,都沒了。
崔永還說,太子元鶴讓我去見他。
10
我其實已經好久沒見過元鶴了。
他已經比我高出一個頭,五官也深邃冷硬了許多,變得很陌生。
元鶴的眼睛有些紅腫,可看向我時,滿目悲愴皆化作憤恨:「你昨夜帶人闖進養心殿,確有此事?」
「是。」
元鶴再問:「你走之后,母親猝然駕崩,我說得可有錯?」
「沒有。」
元鶴盯著我,眼紅似滴血:「你就是罪魁禍首。」
「她失了丈夫,又驚聞泄密一案另有蹊蹺,導致氣急攻心,方才……」
元鶴不等我說完,抬手把我推倒在地,「然后你就暢快了是吧。」
「泄密一案并非我操縱,放火燒屋也不是我所為,你怪我害死母親,不過是找個由頭料理我。」
元鶴怒道:「你怎會信那個叫裴淼的一面之詞?」
「裴淼說的若是一面之詞,司府又怎會被縱火?元鶴,看來你是鐵了心不會去翻案了。」
元鶴冷聲對崔永說:「掌她嘴。」
崔永跪下:「奴才,恕難從命。」
元鶴怒極反笑:「崔永啊崔永,讓你在公主殿服侍上幾年,你不會真當自己是公主殿的人了吧。
」
崔永道:「是。」
元鶴下令:「來人,拖崔永出去,亂棍打死。」
我攔在崔永身前,抬頭說:「元鶴,你瘋完了嗎?」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