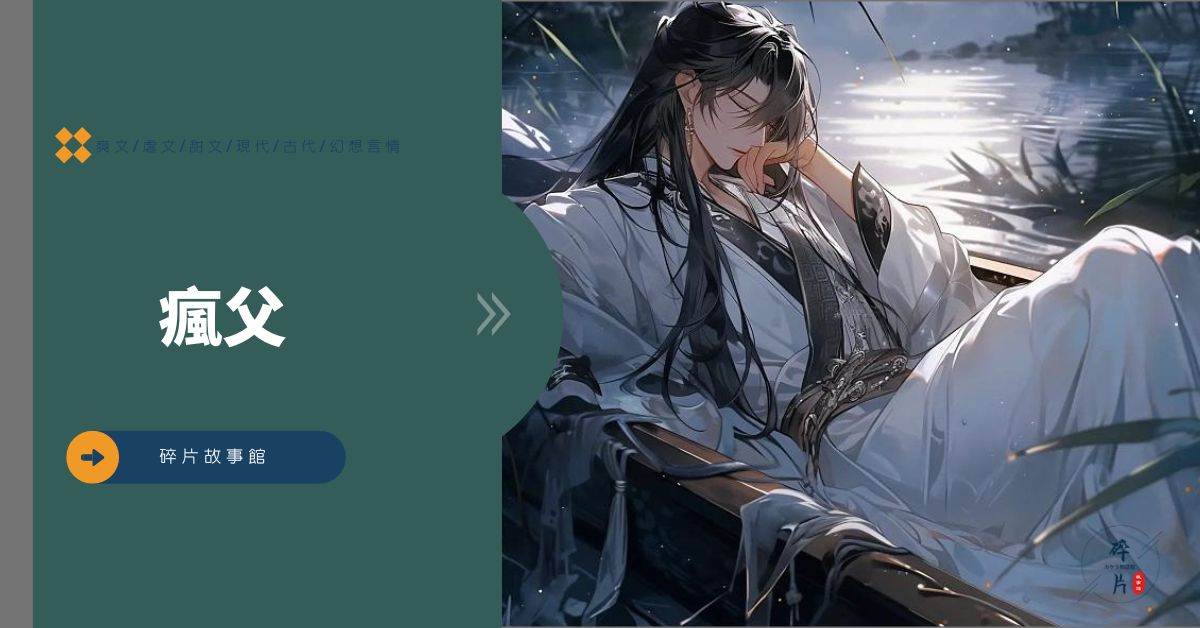《瘋父》第3章
」
她頓了頓,「笨嘴拙舌的。」
氣氛凝固時,灑掃的宮女渾身顫抖著說,她昨夜起來過,經過池邊時,不小心踢到一個軟物,接著就聽到撲通的聲音,但因為天黑看不清是何物,匆匆地就走了。
陛下罰了宮女三十大板。
并且說我御下無能,讓我罰跪。
我跪在庭中,看秋葉簌簌地落。
枯葉落,雪飄飛,沒過多久,又見梨花。
一晃五年過去。
7
我整整五年沒見過父親了。
他被送出宮后是死是活呢?
我好想念他。
深夜的公主殿一片寂靜,忽然間,因為我打翻了酒瓶,鬧出了刺耳的動靜。
這時,綴在簾子邊的玉珠忽然噼里啪啦地碰撞起來。
簾子中央的空隙處露出了一只瘦削的手。
宦官崔永走進來的時候,帶來一身寒氣,凍得玉珠更加激烈地碰撞了幾下。ӯz
崔永看到碎掉的酒瓶時,皺了皺眉。
他正要低身去撿,卻被我一把攥住帽帶,以至于動彈不得。
我乘醉發酒瘋:「讓我見見爹,我好久沒見他了,他還活著嗎?如今還記得我長什麼樣嗎?你,就你,現在帶我去見爹爹,現在就去!」
崔永露出難為的神情。
他抬起手,一根根掰開我扯著帽帶的手,說:「崔永得去請示左相。」
當年御下無能一事后,陛下就把公主殿的宮仆全換了一批。
而崔永則是那時進來的,是左相特意安排。
我知道左相的意思。
陛下所誕子嗣,唯我和元鶴二人。
左相身為元鶴親生父親,自然對我多留了些心眼。
崔永是光明正大地監視著我的。
只是我也無力計較。
我聽見左相二字的時候,酒意清醒了大半。
ADVERTISEMENT
崔永邊收拾碎片邊問我:「公主可喝盡興了?」
「沒有。」
「崔永也就隨口一問,無論公主怎麼答,都不會再呈酒上來了。」
「哼」,我冷笑,「又不是頭一天才知道你們待我散漫。」
崔永嘆了口氣。
他摟來一張毯子給我披著,隨后去把窗子開了個小口,說:[陛下若是突然來看公主,這滿屋的酒氣一時可散不了。]
「陛下多久沒來過了。」
「二十多日了。」
我漫無邊際地說:「我同他快有兩千日未見了。」
崔永先是垂眸思索,抬眼時像是下定了決心。
「崔永偶爾會外出采買,公主躲在馬車里吧。」
我眼睛一紅,問:「他現在安置在哪呢?」
「司家祖宅,就在京城南。」
「不是被抄了嗎?」
崔永說:「確實是抄了,荒廢了許多年,但陛下命人收拾過,現在那里不失清凈。」
8
我停在司府前,隔門聽見了里頭的嬉笑聲。
我很詫異:「祖宅里除了我爹,還住著別人?」
崔永說:「公主見一見就知道了。」
我推開門,看見父親和一個豆蔻少女嬉戲著,他笑著喊:「謠謠。」
不是朝我喊的。
崔永慢慢跟上來,說:「本來瘋了之后便能忘掉全族被屠,親緣斷絕的事,但回到祖宅時發現舉目無親,難免會被激起些回憶。所以前幾年精神更差了,后來還大病一場。左相就送了和公主年齡相仿的女孩過來,騙他說,這就是謠謠。」
我把堵在喉嚨里那句呼之欲出的「爹」給吞了回去。
我對崔永說:「你把她先帶下去。」
「是。」
父親見「女兒」被帶走,看向我時眼神變得惱怒。
后來,這惱怒慢慢被恐懼取代。
他怕生。
已經認不出我了。
我走下臺階,一步步朝父親走去,笑著說:「表哥,你不歡迎我嗎?」
ADVERTISEMENT
父親露出疑惑的神情。
「表哥,我是裴淼。」
萬般無奈下,我借了父親故人的名諱。
當年那個被送去和親的青梅,就是裴淼。
父親的臉上浮現出笑意:「我想起你了,你是表妹。」
我忍不住問:「你都有個這麼大的女兒了?」
父親的笑容愈發柔和:「叫謠謠。」
只是這愉悅忽地就消失了,他有些突兀地繃起臉。
「表妹,我不怕告訴你,其實謠謠并非我的孩子。」
我心中一動。
心想他不至于把我忘得太徹底。
隱約還是記得女兒另有其人的。
不過是敷衍著左相罷了!
我繼續問:「那你的孩子在哪?」
父親輕聲說:「死掉了。」
我微微一怔。
父親陷入回憶的時候,面如土色。
「鈺婉生孩子的那天晚上,我從獄中跑出來了。」
「躲在她寢殿里的那塊屏風后。」
「有端藥的,換水的,人來人往,硬是都沒發現我。」
「鈺婉出了很多血,根本止不住,底下的毯子一張張地被浸透,又再換新的來,因為指頭一直在用力地抓東西,指甲也斷裂了,指縫里全是血。」
「天都快亮了才生起來。是個女娃娃,但她沒有哭聲,剛生出來就沒了。」
父親最后頓了一頓:「然后,我就被押出來了,再然后,他們說我出來時摔下臺階,把腦袋摔壞了。哪有這樣編排人的,我腦袋好得很。」
我木然地指著心口問:「那我是誰?」
父親不解地「啊」了一聲。
我氣得直跺腳,快要哭出來:「你不是說謠謠是你女兒嗎?」
「我和謠謠互相依靠了十數年,她自小就喊我爹,我自然也要把她當女兒看。只是,她確實并非我的親生孩子。」
我不愿意信:「你騙人,你腦袋就是不記事了,所以你編了一個故事。
」
「裴淼,你怎麼了?」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