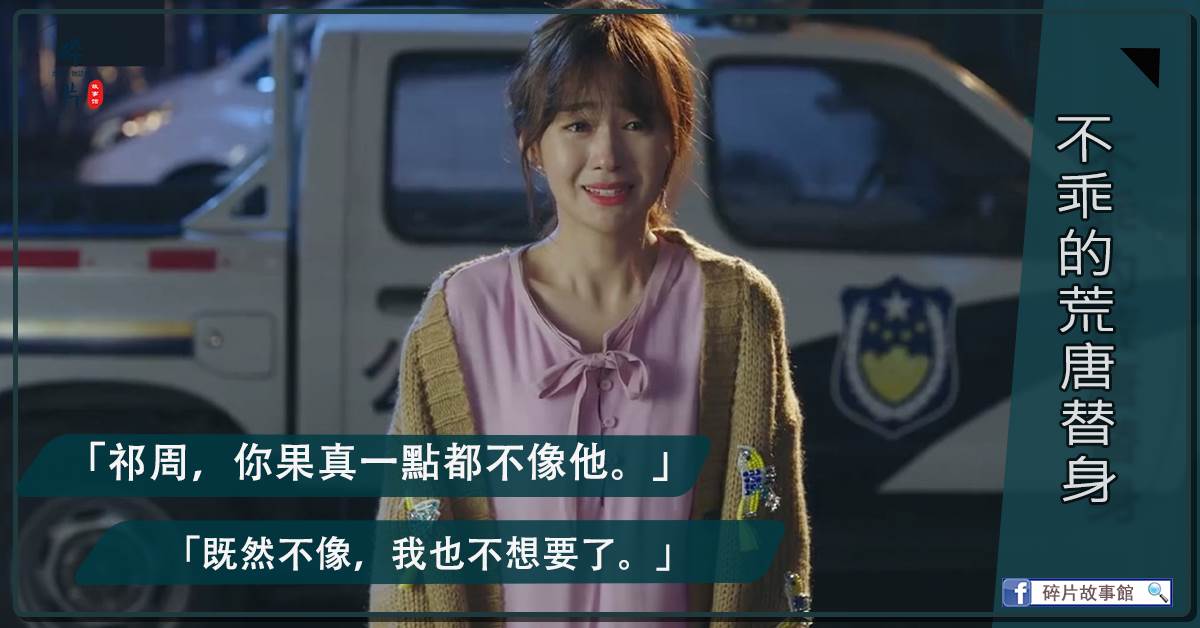《不乖的荒唐替身》第5章
江淮見狀,急著用盡全力推了我一把,嘶啞著嗓子喊:
「杳杳,快跑,別回頭。」
我哭著想去攙他,卻在看到他渾身的傷口后,不知道從何下手。
而且他畢竟是個成年男人,無論我怎麼用力,都拉不動分毫。
最后,他無比虛弱地將手放在我的發頂。
淚眼朦朧中,我聽到他說:
「阿杳,乖一點。」
這是江淮,被救之前,留給我的最后一句話。
后來,他便被送進了手術室搶救。
13
等我從夢境中掙脫,再次睜開眼,人已經在醫院里。
吳苗見我醒來,擔憂不已探過頭來。
「你怎麼樣了?」
我勉強坐起身,問她:
「江淮怎麼樣了?」
話剛出口,我便愣住,混亂的思緒瞬間清醒。
緊接著豆大的淚珠洶涌而出。
我忘了,江淮他,沒能活著走出手術室。
他走的那天,世界一半血紅,一半灰色。
萬籟俱寂中,彩色的祁周從天而降,他和江淮實在是長得一模一樣。
我只一眼便淪陷其中,把他當作了救贖。
吳苗見我哭得上氣不接下氣,慌亂地來哄。
「好杳杳,別哭了,快別哭了。」
我止住哭,從她懷里抬起頭,神色恍惚:「祁周呢?」
她卻神色大變。
我沒看到人,四處打量,不停念叨著。
「祁周不是在住院嗎?他在哪個病房?」
恰好這時,有醫生聽聞我醒來,趕了過來。
我也終于發現了吳苗神色很不自然。
沒得到她的回答。
只能拿出手機打給祁周,可對面機械聲卻傳來:【您撥打的電話是空號!】
我愣住,還真將我拉黑了?
翻了翻之前發來短信的號碼,撥回去。
這時,吳苗的手機卻響了起來。
她慌亂地去捂,但我已經看到了。
ADVERTISEMENT
「你……」
我和她一時間都喪失了語言能力。
那一刻,我看著吳苗的臉,漸漸與記憶中的人融合在一起。
記憶如同潮水般洶涌而來,那一瞬間,我都想起來了。
吳苗是我的閨蜜。
沒有生日宴,沒有求婚,沒有十年追隨,一切都是假的。
江淮讓我乖一點,我便學著努力做個乖乖女。
我以為,只要我足夠乖,就能等到他回來的那一天。
一次次期待中,又一次次失望。
因為。
這世上,再無江淮,也根本沒有什麼祁周。
他只是我極致絕望之下,幻想出來的一個人。
一個和江淮性格完全不同的替身。
我把他幻想成一個處處惹我傷心的浪蕩子,從而用來懲罰自己當年的任性。
而吳苗見不得我這樣,一直在配合醫生幫我治療。
所以,罪大惡極的人,是我才對。
14
我又住院了。
醫生說我病情過于復雜,需要多多觀察。
我開始不愿意開口說話,整天整天地發呆。
來探病的人一波又一波,我卻仿佛看不見任何人,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一次午睡結束,窗前站著一個人。
聽到我醒來,他轉過身,熟悉的眉眼,是消失好多天的祁周。
他歪著頭,一改頹廢地開口笑我:
「你醒了啊,這麼能睡,像只小豬。」
我嗯了一聲,眼眶瞬間就紅了。
「你怎麼來了?」
也許是剛睡醒,嗓音嘶啞,聽不真切。
他大跨步走過來,遞過來一杯水。
「又沒有好好吃藥吧!」
只要沒有好好吃藥,沒有配合治療,我就會看到祁周。
可那些藥實在是太苦了。
我撇撇嘴,很是執著:「你怎麼會來?」
本來以為,不吃藥能見到江淮。
ADVERTISEMENT
時間實在是過去太久了,我都快忘記他的模樣了。
可終歸不能如我所愿。
祁周沉默了片刻,復又抬頭看過來。
「云杳,我來跟你道別。」
我錯愕抬頭,怔愣地望進他的眼中。
祁周笑得和煦,一如我當年剛見他時那樣。
他將水杯塞進我的手中,緩慢地后退一步。
「云杳,既然已經決定了跟過去斬斷糾纏,勇敢地朝前走吧。」
「不要折磨自己了,也不要再回頭了。」
屋外陽光灑進室內,照在他逐漸透明的身體上。
我滴下一滴滾燙的淚,想揮揮手,卻猶如千斤重,抬不起來手臂。
然后我聽到自己說:
「謝謝你啊,祁周!」
「還有,再見!」
15
從這天起,我開始積極配合治療。
每天按時吃藥,按時做心理疏導。
祁周再也沒有出現過。
盛夏來臨之際,我已經恢復正常狀態,可以出院了。
辦理好出院手續后,吳苗陪著我去了一趟墓園。
江淮的骨灰就葬在這里。
我病著的這些年,一直逃避現實,除了他下葬,竟是一次都沒有來過。
可我忘了,他只有我了。
我不來,便沒有人來了。
我眼眶酸澀,抬手輕輕擦拭掉墓碑上面的灰塵。
灰塵盡散,露出江淮清晰的面龐。
照片上的他仍是當初模樣,穩重自持,不茍言笑。
我癟著嘴,邊擦邊喃喃自語:
「江淮,我來看你了,你想我了沒有?」
「你不說說話,我就當作你是默認了。」
「為什麼這些年,你從來不肯來見我呢,是不是還在怪我啊?」
……
「現在,我比你大 6 歲,換你管我叫姐姐了哦。」
說到最后,我已經哽咽到吐不出一個字。
直到日暮西沉,吳苗來提醒。
我才回過神來,站起身。
墓園里除了我和吳苗,已空無一人。
我努力朝著江淮露出一個燦爛的笑,然后朝外走。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