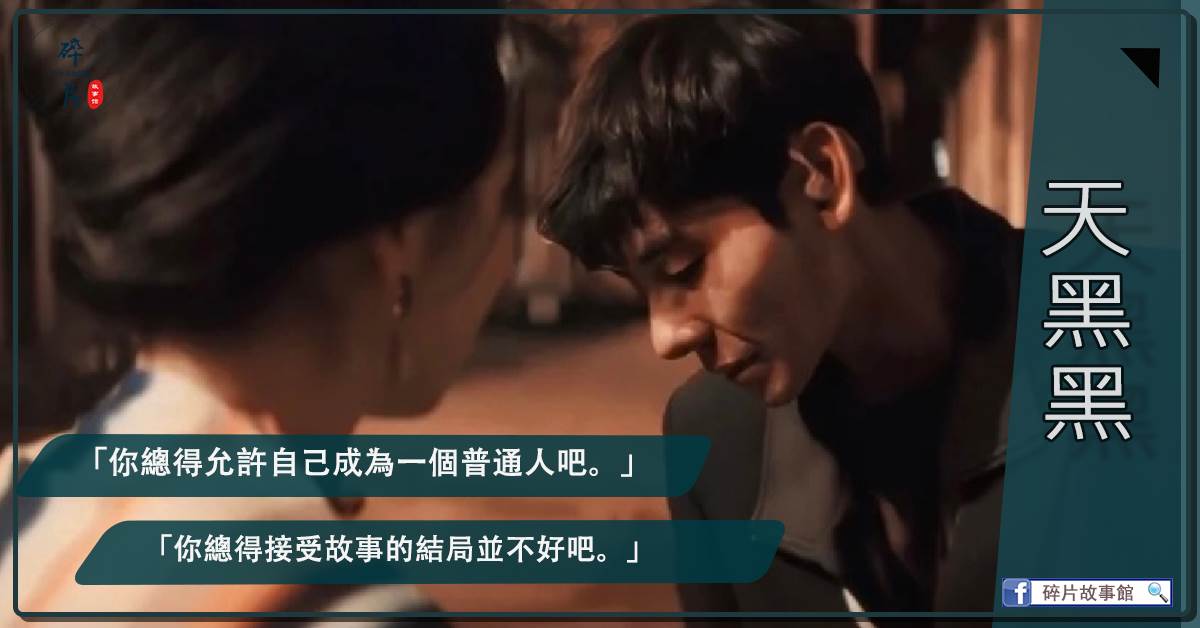《天黑黑》第6章
他真的想烈火的烙印降在他的腦門上。
綻出一道很漂亮的血花。
可是,那可不行。
他死了,我怎麼辦?
……
我問容遠有駕照嗎。
他該死的沒有,我也沒考過駕照,所以我就只能把我的生命付托給他的實踐出經驗。
田野旁的路并不好走,顛屁股程度不比自行車好多少。
而且還挺熱的,我拉開車窗。
曠野自由的風,洋溢進咔噠咔噠運作的車廂內。
晚上好冷,我睡在容遠懷里。
我精神不太正常。
我在思考,其實我從沒有喜歡上秦樹過。
如果容遠像秦樹一樣綠了我。
我會瘋了般沖到他身前質問他。
會死命地想要揪出那個他出軌的女人。
會說分手,會說你這傻 X 到底哪只眼睛瞎了。
但這一切暫時還沒有發生。
不安已經溢滿我的胸腔了。
22
在我拆掉車里最后一罐黃桃罐頭時。
容遠搭著方向盤,略無奈地看著我。
「吃的沒有了。」
「……」
我叼著那瓣黃桃,吞也不是不吞也不是。
他就笑。
說,你不是人質你就是個拖累,你是來度假的,沒了你我還能再多開半程。
我立馬板著臉看他,可是他俯身親過我的嘴角。
我想問他這個牌子的黃桃罐頭糖水好吃嗎。
就聽見他淡淡地說:
「可是我心甘情愿。」
「……」
他說情話很土,一點也不好聽。
車子駛到一處小鎮。
這個鎮子,像是連高德地圖都找不到的地方。
但難保通緝令發不到這里。
現在網絡這麼發達。
容遠又長得這麼好看。
進了鎮子里我才發現,就算是通緝令發到了又怎麼樣呢,這里來來往往的人。
魚攤旁面無表情兜著網的攤主。
ADVERTISEMENT
小賣部靠著門框抽著煙的主婦。
每一張臉,看起來都像是能登在通緝令上的程度。
……甚至連這里的賓館,都不需要身份證登記,多加錢就好。
也正是因為這個「多加錢」,容遠只訂了一間房。
也許我們該買完物資就走。
因為和人多待一秒,就是意味著消息被傳播的廣度多增一圍。
可是,容遠還是揉了揉我的腦袋。
……女人在處理生理上的問題時,有時就是要比男人麻煩許多。
對我來說,泡個澡,靈魂都被洗滌了一遍。
容遠說得對,我就是來度假的。
可容遠不是,他是亡命,他亡命還帶著我這麼一個度假的人。
他想不開了。
他早就想不開了。
23
這鎮子好像夜晚才會恢復生機。
可生機好像也是從腐朽的土地里抽枝出的怪物。
發廊前閃著曖昧的燈。
賓館下人聲喧嘩,大聲地喊著加錢加錢。
容遠叫我乖乖待在房間里不要出去。
他有事要去辦。
我很乖的,我的優點就是乖,可是一直以來,乖從沒給我帶來過什麼。
我的媽媽不愛我,妹妹搶走了我男朋友。
我乖乖等在這個世界的中央,后來發現,我只是被人踩碎了扔泥地里的紙屑。
所以我不想好好活著了。
如果容遠要拋下我,那就把我葬在公路旁好了。
我不希望人死后有靈魂,這樣我就可以當作我從來都沒來過。
……
房間的門口兀自響起鈴聲。
我覺得這不是容遠,容遠帶了鑰匙的。
所以我不打算去開門。
可是門鈴變成了急躁的拍門。
一下一下,然后我聽到了門外中年男人的聲音。
ADVERTISEMENT
「小溪,我知道你在里面,小溪。」
「嘿嘿,你是不是跟那個通緝犯在一起?」
這個聲音,好像可以連根把我的噩夢直接拔起。
這些年,我知道我的爸爸沒死。
因為他甚至每年都會給我打電話找我要錢。
他賭錢肯定又賭輸了,被那些放高利貸的切掉了小拇指。
后來,我不知道他滾去哪里了。
我沒想到會在這里遇見他。
我甚至都不能拿噩夢來形容他,他就是我流膿的傷口。
現在手指插進那里面,慢慢地攪動。
我六神無主地坐在床上,聽見他在門外說:
「嘁,你不開門也沒事。」
「老子準備報警了。」
「嘿嘿,懸賞金一萬呢,夠我,夠我賭一發了。」
「……」
我猛地拉開了房間的門。
顫抖地看他。
我不能讓他報警,我不能,即使他是水蛭,是搗破我傷口的禍首。
這個男人,和我當初見他最后一面時又不一樣了。
我簡直不想承認,我的身體留著他一半的血。
那股骯臟感讓我想當場吐出來。
他氣息虛浮,臉色蠟黃,瘦的好像就只有皮包骨頭。
他噴出來一股煙,我捂著鼻子退后好幾步。
余光瞥見了他胳膊上的針孔。
我猛然瞪大了眼睛。
「你……」
我感覺身體里那一半血在翻涌了,我無意識地顫抖著,我聽見他說。
「嘿嘿。」
「我的乖女兒……」
「你真是爸爸的聚寶盆……」
他上前抱住我,我劇烈地掙扎,他身上臭死了,他明明那麼瘦,力氣還那麼大。
我狠狠地咬在他的手臂上,他吃痛了。
狠狠地甩了一巴掌甩到我臉上。
「操你媽的,給你臉你不要是吧???」
我站都站不住,咳了聲,發現有抹血落在地板上。
他瘋了,他精神不太正常,
他又來上前拖我,我死命地踹他。
「操。」
「老子對你這麼好,你他媽干什麼啊?」
「你是我親女兒!我的骨肉!」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