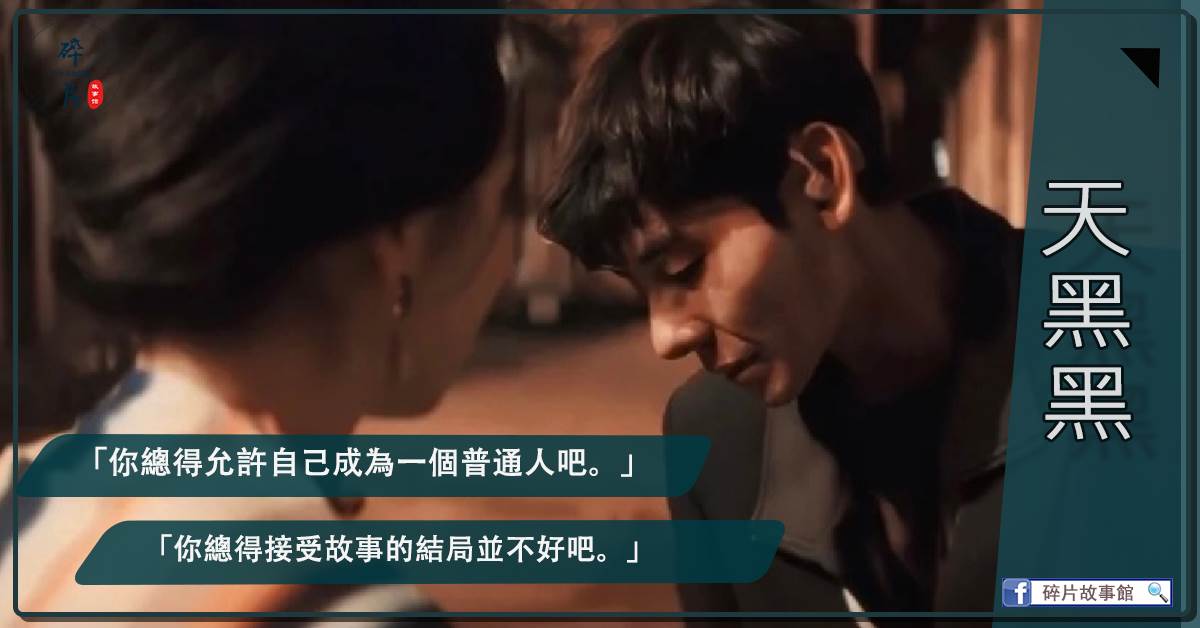《天黑黑》第5章
我猜燒毀那輛車是為了燒毀證據。
也是掩蓋行蹤的一種方法。
我摟著他的腰,在想。
我是他的人質。
我還摟著他的腰。
那我是不是斯德哥爾摩了?
可是不摟著我怕摔下去,這路真的顛。
而且四周黑漆漆的,就算跑,我又能跑到哪去。
我只能摟著他了。
他騎了好久,久到我差點錘他背,說我屁股真的疼死了。
他在一處田地旁的小屋前停下了。
窮鄉僻壤,人都見不到一個的地方。
連路燈都沒一個,這間小屋子卻燃著燈。
容遠隨手把自行車甩在田埂,差點把爬在籬笆旁的黃瓜扯掉下來。
因為響聲,院子里的狗起來了。
汪汪地叫著。
在夜空中賊響亮,卻不是那種對外敵的叫。
好像……更偏似一種討好?
我看見容遠俯身揉著那幾只狗的頭。
「我草?」
「容遠?」
「你他媽還沒被逮住啊?」
屋里走出來一個大叔。
大叔揉著腦袋上上下下打量我,跟看見外星生物似的揉眼睛。
「我草,這誰?」
容遠回答他。
「警察來逮我了。」
「她……是我人質吧。」
「……」
「你小子,他媽的。」
大叔扇了容遠腦袋一巴掌,容遠沒躲。
「你考慮過人家的安全嗎?」
「……」
我還在糾結,綁匪在思考安全是不是遵循人道主義時。
籬笆的圍欄開了,容遠走了進去,我跟在他身后。
我聽見容遠淡淡的嗓音。
「黎叔,麻煩你了。」
「明天幫我把她送到鎮上吧,她乘公交車應該就能自己回去了。」
「……」
我的第一反應,不是我不是人質了。
不是我要乘哪路公交車。
是容遠要丟下我了。
我上前拽住他的手腕,問他。
「你去哪呢?」
容遠總是愛朝我笑。
ADVERTISEMENT
他笑起來淺淺的,淡淡的。
他抬手揉我的頭發,溫柔,小心。
「逃亡啊。」
「我總不能一直讓你做人質吧?」
19
我坐在田埂旁。
夜風挺舒服的,黎叔給我泡了一碗康師傅牛肉面。
他在我一旁抽煙。
薄薄的煙味飄進天野里。
「你惦記那小子干嘛?」
「他是殺人犯啊。」
黎叔嘿嘿地笑著。
「你猜他殺的是誰?」
「他爸爸。」
「就這樣,一斧頭,一斧頭地砍下去。」
「誒唷,當時那場面,血都濺了兩三米,他還在砍,還在……」
黎叔描述得很有畫面感,我打了個寒顫。
見我躲,他又笑了。
「因為,你知道嗎……」
黎叔欠身,煙頭被摁滅在我身旁的柵欄上,
「他爸爸,當著他的面。」
「強奸死了他親姐姐。」
「……」
黎叔抖著不成調的話,繼續說。
「所以有的人,活著不就是煉獄嗎。」
「是要在刀子上行走的,是萬劫不復的,是毫無光亮的。」
「誒……看不到希望吧,好可悲。」
他蹲下身,摸著湊在他身旁的土狗的狗頭。
「你說是吧,大黃。」
「可悲吧。」
「太可悲了。」
20
我在車子那找到了容遠。
就是停在院子里的那輛車,好臟好老,車牌是套牌。
容遠明天要開這輛車走。
他今天睡在了車里。
我鉆進了副駕駛。
容遠睡在駕駛座上,搭著從黎叔那順來的羊皮外套。
全是煙味。
和容遠身上的味道一點都不一樣。
我湊近他,他睫毛輕顫了顫。
我說,你不要裝睡。
他就睜開了眼。
好好看的眼睛,像是把我的黑夜裝在了里面。
像流淌的深海,湮滅在一片潮汐里。
他拿鼻尖頂了頂我的鼻尖,
笑了,問我。
「怎麼了,想我啊。」
「不要想我。」
「人生就是這樣,我們都是過客。」
「總會錯過的。
ADVERTISEMENT
」
「……」
我壓在他身上,垂著眼看他。
「帶我走吧,容遠。」
他笑著抬手揉我的發尾,乖,別鬧。
「……」
我盯著他的眼睛,在他面前解開衣服。
他坦蕩蕩地望著我。
夜色忽而卷入一片紛雜。
我沒脫光,但這樣,足以讓他愣住了。
這是我頭一次在異性面前展示我的身體,連秦樹都沒見過。
秦樹總以為我是清高,不讓他碰我。
其實,我很怕。
很怕這樣一張殘破的身體,他看到會驚訝,會害怕。
淺淺交錯在一起的,少有增生的,丑陋的疤痕。
遍布在我的身體之上。
板條抽的,煙灰缸砸的,煙蒂燙的,鋼尺打的。
好多。
承載著我年少時幾近被摁進地獄里的回憶。
我輕輕地朝他說。
「我不想回去了。」
「我做了那麼過分的事,我媽肯定不要我了。」
「秦樹會報復我的,我妹妹也會。」
「我如果找我爸的話。」
「他會打我的。」
「他打我好疼,疼死了,我……」
我猛地被人摟進了懷里。
我果然好喜歡他的懷抱,好暖和,我就是貪戀他身上的溫度罷了。
我不知道。
世界把我逼仄成很小的一塊,我不想逃,直到遇到容遠,我又想逃了。
我覺得他如果能逃的話,我也能逃的。
我好喜歡他。
我覺得這種喜歡是。
原來你也跟我一樣缺胳膊少腿啊。
的那種喜歡。
21
臨走時,黎叔給了容遠一把拿黑布包著的東西。
我知道這玩意既不合法又不合規。
光天化日下拿出來,都會被人沖出來制服的那種。
可我又是第一次見到這種東西。
被黑布遮著。
據說扣下扳機,里面鋼制的玩意就會飛旋出去。
我問容遠。
「這家伙是真的嗎?」
他就讓我握著這東西,然后頂在他的額頭。
「你要不扣下扳機試試看?」
「……」
說這話時,他一瞬不瞬地望著我。
我突然就知道了他那一刻真的想要我扣下扳機。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