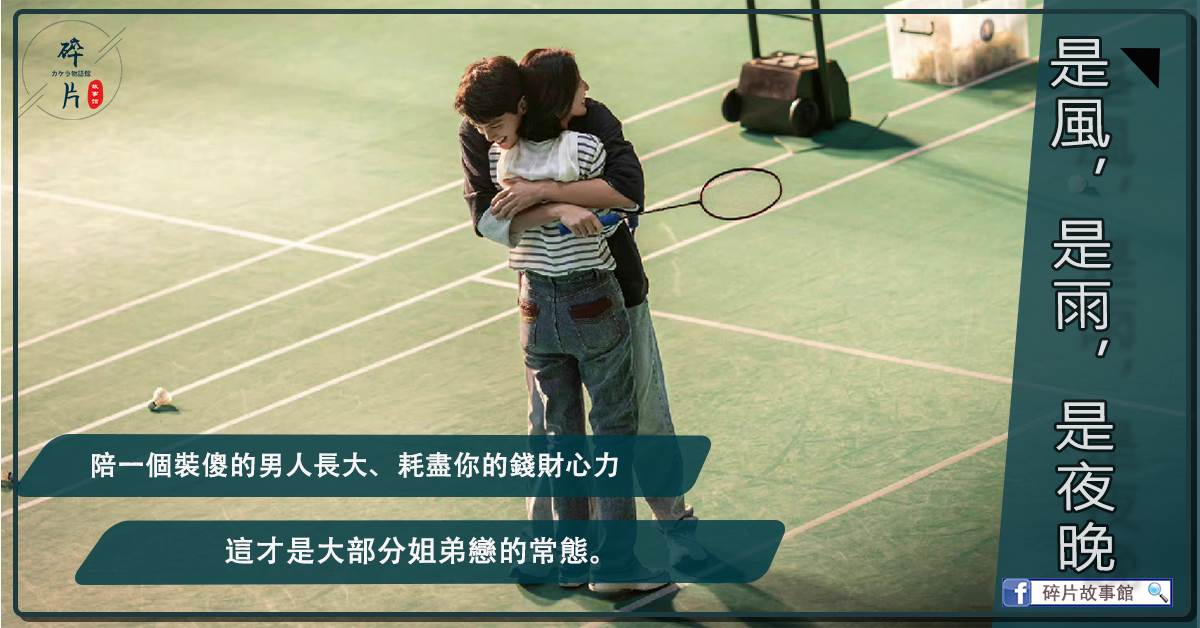《是風,是雨,是夜晚》第7章
」
【八】
孟齊和我耍小孩子脾氣,說不去住賓館,他寧可在我單位門口站一夜。
沒有辦法,我把他帶到我租的房子里。我給他整理了客廳的沙發。
他的鞋被雨水打濕了,光著腳抱膝窩在沙發上,看著越發像一只被丟棄的狗狗。
我問他突然來找我,家里人知不知道,他小女朋友知不知道。
他說因為疫情,他爸讓他不要出國了,就之前的學校接著念就好了。
他媽媽知道他來找我了,他爸爸在外邊做生意,可能還不知道。
「我和她分手了。」他的手下意識揣進兜里,想摸索一根煙出來。
但我丟給了他一顆糖,他就剝開塞進了嘴里。看來這事兒真讓孟齊沒少焦慮,他摩挲了幾下沙發,站起身又坐下。
「我其實一開始就知道她圖什麼。去俄羅斯的時候,她過生日,我想著她爸和我爸是朋友,我就給她買了幾萬塊錢的禮物,那之后她就很粘著我。」
「她明明知道我有女朋友。」
但她依然很主動,陪他在酒吧晃蕩,從天黑燥到天明。在他最煩悶無依的日子里,她給了他恰到好處的陪伴。
小孩子就是這樣,只關心那些能握在手里、擺在眼前的好處。他們很少長遠看權衡利弊。
「姐姐……」孟齊雙手捂住臉,寬大的毛衣袖口露出細白的手腕,「她問我為什麼親她的時候喜歡叫『姐姐』,明明她比我小。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我根本離不開你……」
「我一直都很想你,我夢里都會夢見你。我在俄羅斯那邊,宿舍樓后邊有片白樺林,我夢見你來找我,我背著吉他給你唱歌,唱了好幾遍<夏夜晚風>。
ADVERTISEMENT
」
我從沒這麼矛盾過。可這種情緒上的被需要,實在讓我忍不住追逐。
一個人獨居他鄉,三十歲獨自拼搏。
我夢想著事業愛情兩全,有朝一日榮歸故里,可家里人說得最多的只有:「趕緊回來,找個家跟前能過日子的趕緊結婚。都沒人要的老姑娘了,再耽誤,到時候生孩子都麻煩。」
同事隔著利益往來,朋友也各有各自的煩惱。
孟齊這份簡單的依戀,實在讓我這樣平庸的人舍不得放手。
于是我和他復合了。以送給他那把定制吉他為標志,他在我床邊打了小半個月地鋪,說真想就這樣陪我一輩子。
那之后換他奔波了。平常上學,節假日的時候趕來我的城市,甚至我住的小區附近的一家酒吧都被他混熟了。
每回來了他都在那里駐場,只唱我點的歌。
我問他之前組的樂隊怎麼樣了,他笑著揉揉腦袋,模樣總是乖乖的,「我爸當時不是逼我出國了嗎?他們就重新找了一個吉他手兼主唱,我就沒人要啦。」
他會抱著我送他的吉他,用那雙亮晶晶的圓眼凝視我:「還好姐姐還要我,這才是最重要的。」
孟齊這一次回來,看上去真心篤定了許多。
他真的有考慮和我在一座城市發展,他在結交這邊搞樂隊的人。
但比起之前和同學、發小一起搞,陌生的地方總是龍蛇混雜。
于是之前從不陪酒的孟齊,有時候會在和我坐了一會兒后,移步另一個桌子。和我沒見過的男男女女推杯換盞。
有時候我周六加完班,累得只想席地而睡的時候,還得去酒吧把醉醺醺的孟齊拖回我租的房子里。
ADVERTISEMENT
我說他腸胃炎越來越嚴重了,真的不能再這麼喝酒了。
他捂著肚子倒在我懷里,煞白的側臉上沒有表情,「為了姐姐,都值得。」
不免愧疚,我問他我何德何能。
他想了好一會兒,他說是一種安穩感和歸屬感。有我在的地方,就和家一樣。
那之后我更不忍心和他提諸如少喝酒、少去酒吧、多花心思在學習上這種話。
我心里隱約覺得有問題,但我總會覺得,只要真心換真心,結果不會差的。
然后他大二學年的學分就沒有修夠,之后得延長畢業重修一些必修課。
因為這個事我有點賭著氣,但真正點燃我的,是孟齊毫不在意的態度。
他說反正搞音樂又對學歷沒要求,吉他彈得好比高數學得好更重要。
「這一點你真的不如夢夢。她就覺得人能做成一樣事就夠了,何況我做的還是我喜歡的事。」
他拿著我的杯子,煮著我買的咖啡,指點著我的人生。
「姐姐,我覺得你永遠不會懂這個。哪怕你念了個 985 出來,不也沒能力做自己喜歡的事嗎?」
我理虧,無法辯論。
于是原本想就這個話題,問問他打算什麼時候娶我,也就這樣咽回了肚子里。
【九】
陸宇明聽了我和孟齊的這些事,說我已經控制不了了。
他說當時我說只有我玩孟齊的份,顯然已經不是了。
我始終垂著頭,不置可否。孟齊不喜歡我和陸宇明來往,我只敢在午休的時候,趕來陸宇明所在的公司和他喝杯茶。
這一年我三十一歲了,因為孟齊的事我和家里鬧得很僵。我只會偶爾和還在上學的弟弟妹妹寒暄幾句,給他們打些生活費。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