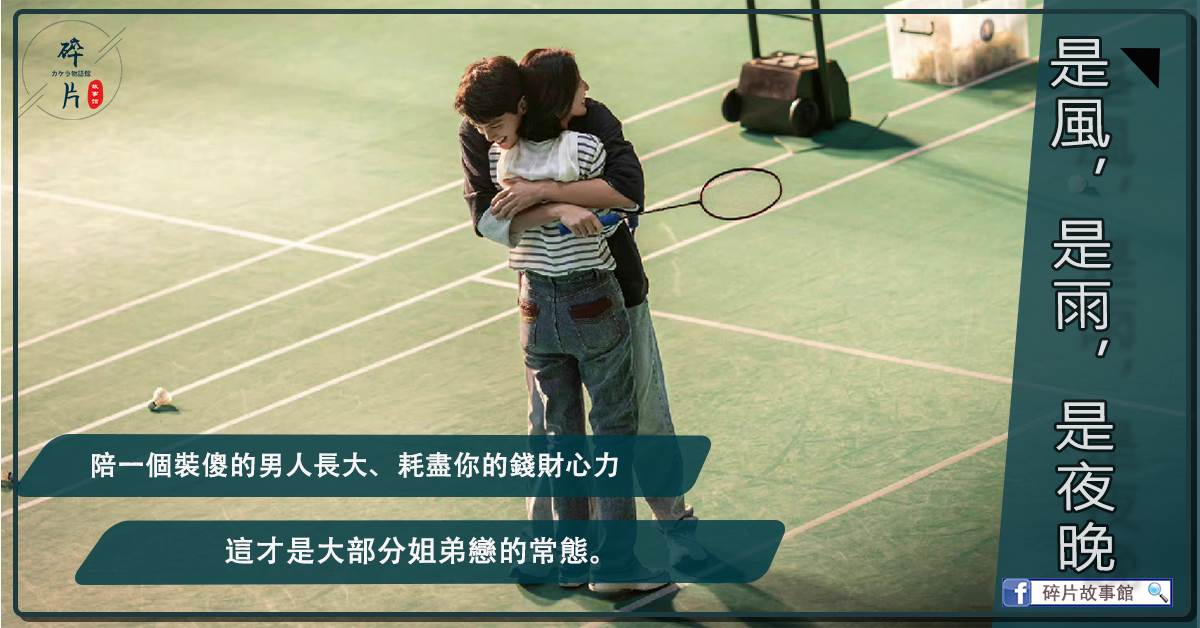《是風,是雨,是夜晚》第5章
」不知道陸宇明想起了什麼,只知道我們這個年紀的人,一聊起感情都容易沉默。
陸宇明最后也沒給什麼建設性意見。但他同意我說的,重要的事至少當面講清楚。
以及讓我清醒一些,該執著的執著,不該執著的及時止損。
「孟齊就是個小孩子,能把我怎麼樣呢。我比他多吃八年飯呢,我不欺負他就不錯了。」我如是胸有成竹地說,但抬頭看見那輪月亮,還是忍不住地牽心。
那個只知道彈吉他、寫曲、唱歌的小孩。我會忍不住擔憂,他現在一個人在俄羅斯,有沒有吃飽、有沒有睡好。
有沒有和我想念他一樣想念我。
【六】
臨近年末的時候,我想起孟齊之前碼住的一雙潮牌鞋子。頂我兩個月工資了,但想著再見面的時候能順利挽回,我還是一咬牙買了下來。
我摸索到了他的微博賬號,很偶爾他會發一條動態。要麼是聽歌的,要麼是拍的風景。
配的文案大多孤獨,我也不敢打擾他,只是默默看著。
然后就是年底疫情大面積的爆發。
我實在擔心得不行,問了林阿姨,才知道孟齊買到機票回國了,已經到家了。
她當時很隱晦地回我:「現在疫情很嚴重,小梁你也注意安全。孟齊挺好的,他也希望你過得好。」
我也是心急了,沒細想,以為是孟齊在給我臺階下。
于是我用另一個電話號給他打了過去,熟悉的聲音透過聽筒傳來時,我才知道我有多想他。
我輕咳了一聲,他試探性地叫我:「姐姐?」
「嗯,」我啞著嗓子應他,思緒幾轉,最后只是說,「回家了就好。
ADVERTISEMENT
」
我沒想到他當時就哭了。他連叫了幾聲「姐姐」,然后說很想我。
我們加回了微信,他并沒有更新太多朋友圈。
最顯眼的,不過是換掉了之前拿我們的合照設置的背景。
我們開始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雖然陌生了許多,但我覺得能重新有個開始就是好事。
因為疫情影響,這個年我是在我租的房子里過的。我沒能回家,大年夜給爸媽打視頻。
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和我弟我妹坐了一大桌,我抱著被子窩在停電的屋子里,眼眶酸得發脹。
他們問我好不好,我說挺好的;問我有沒有囤吃的,我看著冰箱旁邊的兩箱方便面說囤了;問我有沒有人照顧,陸宇明在不在跟前。
我說他確實也因為疫情沒回去,但我倆不在一個小區,也串不了門。
而且我和陸宇明真的純朋友。以前不會談對象,以后也不會。
我媽最了解我,突然問:「你是不是還和你之前認識的那個小男娃聯系呢?」
我悶悶應了一聲,我媽一向脾氣大,劈頭蓋臉就罵我不長腦子。
我爸攔了一下,說年輕人的事不要管那麼寬,我媽一句話直戳我肺管子:「過完年你就三十歲了!人家富二代,還是啥、搞音樂的?你玩得起嗎你?」
「我沒玩……」
最后是在我的哭腔里草草結束了對話。滿腔委屈,我給孟齊打了微信視頻。
響了幾聲之后,被掛斷了。
我情緒有些崩潰,給他發了一大串話。
過了好一會兒,他簡單回了幾個字:「在吃飯,晚點聊。」
我發的消息是綠色背景,他發的消息是白色背景。
ADVERTISEMENT
我看著上邊大片的綠色夾雜個別幾行白色,我漸漸就冷靜了下來。
我這才有些后悔。他肯定不喜歡看到我剛才那種失態的樣子。
但我依然無法入眠,我一直等到凌晨兩點,等來了他的信息。
我問他可以打電話嗎,他說他爸媽睡了,臥室門對門,不方便。我說那我們就打字。
但只是寒暄了幾句客套話,他就又消失了。
我盯著屏幕又等了半個小時。凌晨三點,整座城都悄寂了,我寫了刪刪了寫,最后只發了句「晚安」,然后只能去睡覺。
那之后我就有了半夜驚醒的毛病。
起因只是怕錯過孟齊的信息。
我甚至把鈴聲調到了最大。
這樣的情況,一直延續到了第二年四月,管控稍松之后。
我特意請了年假,我想給他驚喜,帶著我給他買的鞋直奔機場。
我是在去機場的路上,才給他發的消息。航班截圖發過去,請他方便的話就來接一下我。
那是孟齊難得地主動打電話給我:「你要來看我嗎?」
語氣很震驚,我忍俊不禁,「對啊,我想見見你。」
他突然問我:「你打算用什麼身份見我?」
這話問得我有些不知所措,我想了半天回他:「就當老朋友吧。」
我并沒有細想,他當時好一會兒的沉默代表什麼。他最后只是說讓我路上注意安全,他這就出門去機場。
他親自開車來接我。
我在出口看到那熟悉的身影的時候,實在沒忍住,跑出去抱住了他。
是熟悉的甜暖清香。我的眼淚很不爭氣地流下了,他扭著頭,也悄悄抹了下眼睛。
他習慣性拿過我的包,甚至習慣性牽起了我的手。
他帶我去停車場,坐上車的一瞬凝視著我說:「姐姐。你是用『姐姐』的身份來看我的。」
我疑惑地看著他,清晰地看到了他眼中的糾結與愧疚。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