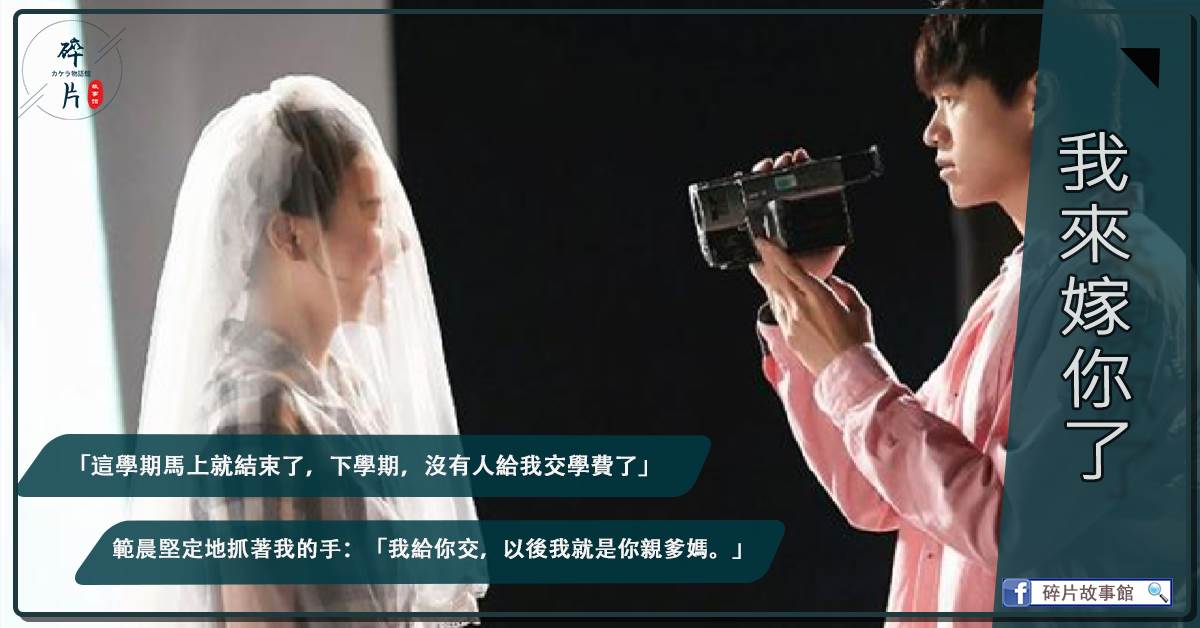《我來嫁你了》第2章
學姐蹲下來拍拍我的臉:「我不來找你你還自己送上門來了。」
是那件事,我諾諾開口解釋:「那是個誤會......」
話音未落臉上就挨了重重的一巴掌,打得我腦袋嗡嗡的,我感覺自己的半邊臉瞬間腫起來了。
我求救般地看著程路遙,他皺了皺眉,低聲說了一句:「走了雨晴。」
謝雨晴壓根兒沒理他,反向又是一個巴掌甩過來。
我拼命地躲,使勁兒把她推開,謝雨晴倒退兩步,踉蹌了兩下。
她瞪著眼睛:「你敢推我?」
我大聲叫:「那天那個事是個誤會,我對學長真的沒有......」
肚子一陣劇痛,謝雨晴猛地一腳踹向我的肚子,我捂著肚子怕自己今天死在這兒。
她揪著我的衣領:「你怎麼還不明白?明明是一只山雞非要湊到鳳凰堆里來,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樣子。」
我再沒有說話,也沒有求饒,我想我明白她的意思。
我這種沉默話少,懦弱膽小又是農村來的孩子,就是他們的欺負對象。
哪怕沒有上次那件事,我在學校的處境也沒有多大改變。
我抓緊了手指,謝雨晴還準備動手,被程路遙拉著走了,我蜷著身子靠在墻邊。
我想回去了。
我不想在城里了。
范晨哥哥。
我想你。
3
就這樣頂著校園霸凌直到初二的暑假,奶奶去世了。
奶奶從小在棗村長大,爸爸希望她能回歸故土,帶著全家人和奶奶的骨灰重新回了棗村。
將奶奶安葬好后,我迫不及待地跑回之前的家,我想找范晨,我想告訴他我在城里的一切,我想告訴他奶奶走了我有多傷心。
ADVERTISEMENT
但遺憾的是范奶奶告訴我他已經很長時間沒回家了,初中畢業后他就沒上學了。
我帶著失落回到城里。
奇怪的是從某天開始,我時常感覺有人跟著我。
這天周五,我走在巷子里的時候,被跟蹤的感覺越來越強烈,我加快了步伐。
腦袋上用礦泉水瓶砸了一下,謝雨晴和她的小姐妹們以及我們班的班長站在我身后捧腹大笑。
我在心里嘆了一口氣。
我已經做好了挨打的準備了,站在墻邊緊閉著眼睛,等待著熟悉的拳打腳踢。
下一秒卻聽見謝雨晴的大罵:「他媽的誰!誰砸老娘!」
我睜開雙眼,映入眼睛的就是站在巷口那個男人。
他戴著一頂黑帽子和口罩,看不清臉。
謝雨晴從地上抄起一根棍子就朝他走過去。
「我看你他媽是不要命了!」
棍子還沒有掄到那個人身上,只見他靈活地一躲,反手就把謝雨晴的棍子搶了過去,一棒子打在她的腰上!
她的那些小姐妹見狀紛紛圍過去,但好像又被他身上的凜冽氣勢嚇到。
「你,你怎麼能打女人?」
我們班長壯著膽子質問他。
我聽見他輕輕地一聲冷笑,反手又是一棍子打在謝雨晴的腿上。
謝雨晴的尖叫響徹整個巷子。
另外一個女生沖上去,直接被一棍子打得雙膝跪地。
「滾。」
他的聲音很低,又帶著強烈的煞氣,幾人連忙把哀嚎的謝雨晴拖著走了。
巷子里瞬間只剩下我和他兩人。
他給我的感覺太過于熟悉,那個名字就在我的嗓子口立馬就要脫口而出。
他直接轉身,也沒跟我講話,我鬼使神差地跟在他身后。
ADVERTISEMENT
走了大概二十分鐘,他進了一個汽車修理廠。
我再想走近時,他已經消失了。
是他嗎?
幾乎瞬間我就給了自己答案。
就像平靜的湖水忽然被大風吹過,我壓抑許久的心里突然生出了期待。
從那天以后,我每天放學都會去那個汽車修理廠,在旁邊的石凳子上寫作業,盡管他從來不跟我講話。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來了城里,看到我又為什麼不跟我相認。
就像是我們兩個之間的默契,我每天下午都能看到他,他也能看到我,但我們兩個月來,一句話都沒說過。
自從上次謝雨晴被打后,她們就再也沒找過我麻煩,這兩個月的日子,比我之前過的兩年都要開心很多。
就跟小時候一樣,只要有他在身邊,我就覺得安心。
可是生活不是電視劇,它遠比電視劇精彩多了。
4
修理廠門前的馬路沒有紅綠燈,我被一輛飛馳的汽車撞飛到空中,閉眼前只看見范晨急促的身影和蒼白的臉,叫著我的名字。
「豆豆!」
這場車禍沒有要了我的命,它帶來的后果對我影響卻更大。
因為失血過多需要輸血,爸爸愕然發現 B 型血的自己和 A 型血的媽媽生出了 O 型血的我。
他們在醫院大吵大鬧,才暴露出原來我不是爸爸親生的,我只是媽媽當時犯下的一個錯。
爸爸留下了我的住院費和一紙離婚協議,不知去向。
媽媽也不知所蹤。
當然,這些都是范晨告訴我的,因為我醒來的時候,身邊就只有他一個人。
我開口說話還有點艱難,只是安靜地聽著他講述這段時間發生的事。
說實話,太狗血了,我反應不過來。
依稀有點模糊的記憶,媽媽在我床邊一直哭,一直跟我說對不起,那個時候我想睜開眼睛把她的眼淚擦干,告訴她不要哭了,但是我睜不開。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