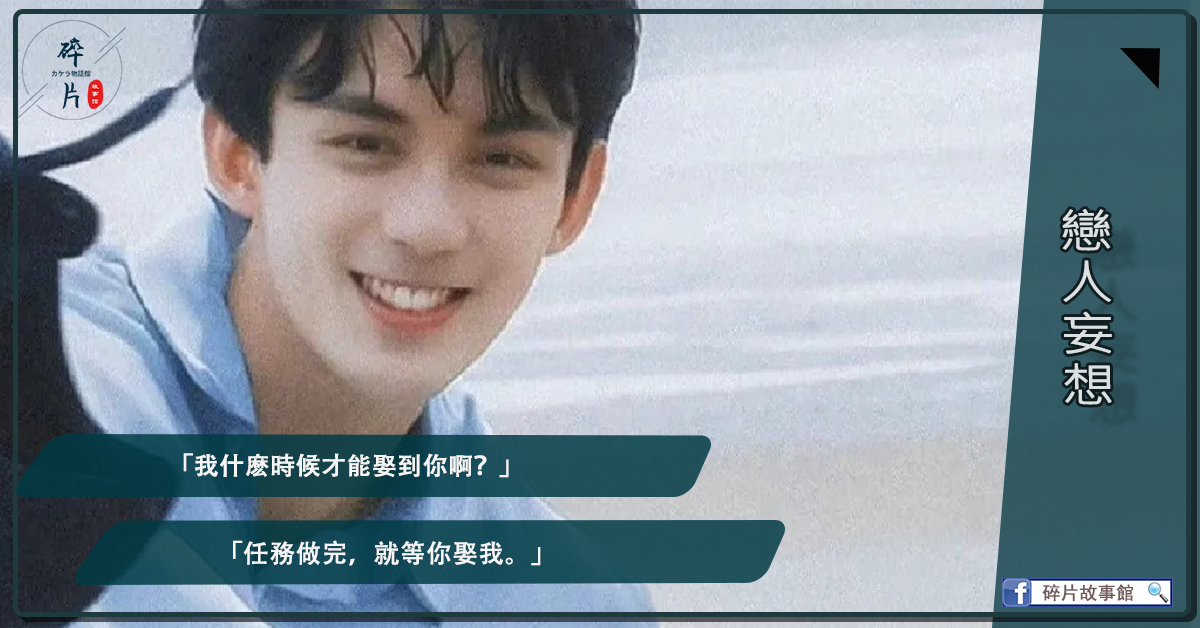《戀人妄想》第4章
江婷是一枝花,她大張旗鼓地追著林敘。
可林敘,每次,都把我護在他身后。
「我告訴你,不要在我老婆面前說一些引人誤會的話。」
「我喜歡的就是張婧年,我命給她我心給她我腰子也全掏給她了……」
……
視線晃動,我的目光,又流連到站在一旁的林敘身上。
江婷說,是他給她開的門。
原來,現在的他,是不會拒絕江婷的。
我忽然覺得心上卷起無端的怒火,憑什麼呢,憑什麼啊?
一直照顧著你的人是我,憑什麼要把我當作惡人,憑什麼要推開我,憑什麼要拿這樣若無其事的表情看著我。
我要死了,你知道嗎林敘。
我也會難過的,林敘。
不是說最喜歡我嗎,那為什麼要拿這樣毫不在意的眼神看著我。
為什麼被推開的是我,就這麼恨我嗎,就這麼迫不及待地想要擺脫我嗎。
我猛地拽過林敘的衣領,將他推向了門外。
「你走!你跟著江婷走!」
「我們這輩子都不要見面了,我不管你了!」
「我再也不管你了!」
那是林敘從案發現場被接回來后,我第一次朝他兇。
這麼多年,無論他對我做了什麼,他把我當成了什麼,我都沒有兇過他。
于是,恍然間,我好像看見他有一秒的失措。
那兩個人被我轟出門外,我靠著門,感受著自己轟隆隆作響的心跳。
口袋里,四四方當疊的那張紙,被我胡亂地揉碎。
我的手指掐進掌心里,捂著自己疼地紛亂的腦袋。
林敘,我再也不管你了。
你想要我管你,我也不管了。
9
音響店里,還在放著七八十年代的歌。
窗外大雨磅礴,豆大的雨滴奮不顧身地沖刷著玻璃。
ADVERTISEMENT
「高音甜,中音準,低音沉。」
坐在我身旁的人,閉著眼,身子隨著音調的起伏而擺動。
「總之就是一句話,通透!」
我在音響發出的高昂歌聲中嘆了口氣,對他說:
「阿舟,我要死了。」
音響店陷入戛然而止的寂靜,他直起身先看了我一眼,然后再垂眼看我遞過去的紙張。
半晌,聽見他吸了口氣的聲音。
「治不好了?」
「我會配合治療的,但治好的概率不大。」
「林敘呢,他怎麼辦?」
「……」
身旁的人支著額頭問我,而我陷入了長久的沉默。
「他……很好。」
「我把他交給了能把他照顧得更好的人。」
這些年我,還有局里,都從沒有間斷過給林敘的治療,可有一點不得不承認。
這次江婷請來的心理醫生,比我想象的要更好,是頂尖的醫學專家。
是,按照林敘現在心理醫生的說法,如果我一直陪著林敘,終有一天我能等到他康復,這只是時間的問題。
可……我沒有時間了。
命運就像跟我開了個巨大的玩笑一樣。
「你的委屈就差寫臉上了,年姐。」
面前的人毫不客氣地戳破了我的謊言,我的從容。
李舟,是跟林敘同期的臥底。
他潛伏的程度不深,所以也不像林敘那麼難以自拔,任務結束后工作了幾年,就退役了,開了這家音響店。
我吸了吸鼻子,看著他的眼睛,說:
「我死后,把我的東西葬在青城山腳下,跟他們葬在一塊。把我的骨灰做成煙花,放在天上。」
「……」
大抵是我安排后事太過認真,李舟的臉上才慢慢染上嚴肅。
「別啊,年姐。」
「你要是真死了,你真死了,我怎麼跟林敘交代?」
「他要是恢復了記憶,不得心疼死你?」
ADVERTISEMENT
「張姐,你得撐著啊,你得撐著到林敘那崽子想起你。」
「然后給他一大逼斗,那沒良心的……」
一聲天雷,轟隆隆地在不遠處炸響。
我扯了扯嘴角,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昨天晚上回到家的時候猛地跌倒在玄關,頭疼得厲害,后來一個人躺在地板上,躺了三個小時。
被冷醒,我才發現連夢里我都在喊林敘的名字,嗓子都喊啞了。
可林敘不在了。
傾盆而下的暴雨沖刷著我們的距離,直到我的手機鈴聲震起。
是江婷打來的,我接了。
電話那邊的聲音很急促,我猛地站起來,去找傘。
李舟問我,發生了什麼。
我關掉手機,茫然地看著他。
「林敘失蹤了。」
「你說,我為什麼還是這樣想拼了命去找他呢?」
10
林敘有很嚴重的心因性偏執性精神病。
我怕他把朝他飛馳而來的卡車看成晃晃悠悠的云彩,我怕他把對著他的槍管看成美味的冰淇淋甜筒。
對于常人來說普通的世界,于他來說卻有可能危機四伏。
這也是我關著他,不讓他出門的原因之一。
我和江婷的人手匯和,然后從她住宅方圓百里開始摸查。
剛在警局實習的時候,其實干的最多的活就是找失蹤群眾。
可我那時卻不知道,原來找一個對自己來說重要的人,會這麼慌亂。
本來打著傘在雨里跑的,后來覺得太麻煩就把傘給扔掉了。
心臟不停地跳,視線流連過一個又一個霓虹的燈牌。
明明說好再也不管他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問自己在干什麼。
就找這一次就好了,就一次,再管他這麼一次。
因為好像看見了熟悉的身影,我不管不顧地向前,卻撞到了從拐角駛來的自行車。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