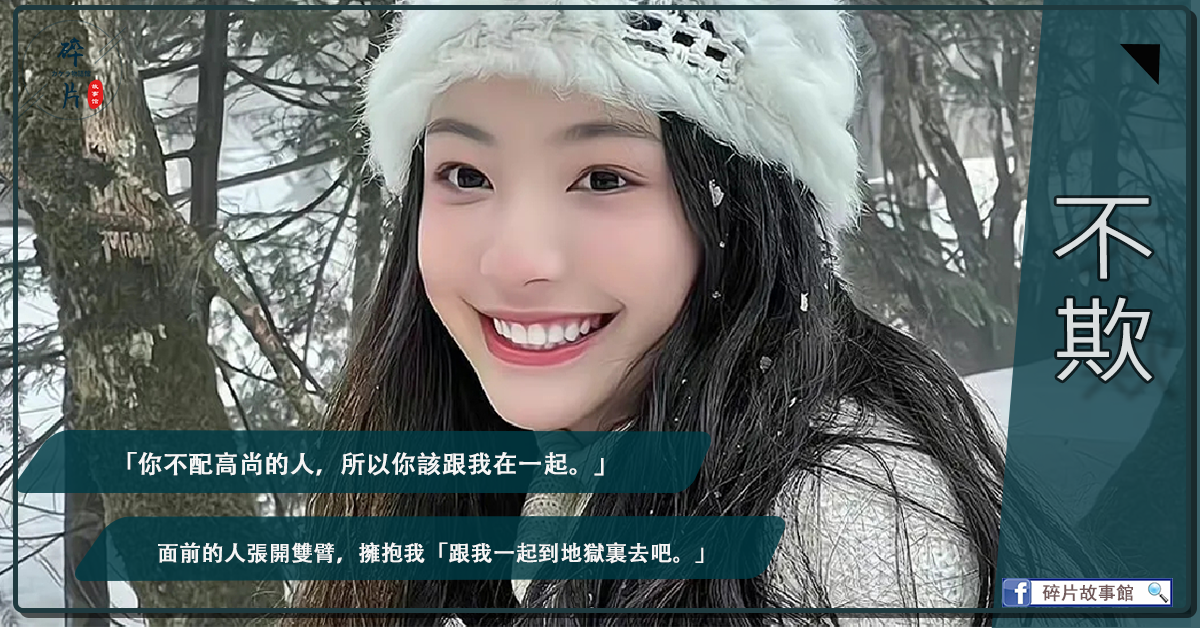《不欺》第5章
「你忘記你是怎麼玩忽職守,怎麼推卸責任的了嗎?」
「……」
我的這兩聲質問下來,全場鴉雀無聲。
然后,我聽到一個很年輕的聲音。
「你在說什麼呢?王老師怎麼可能是這樣的人。」
「你要是再這樣隨口潑臟水,我就喊保安來了!」
一個戴著眼鏡的男大學生過來拉我的手臂,我沒想到,他這樣的人,現在也有學生尊崇。
更無恥的是,臺上的人,特意表現出一副風度翩翩的樣子。
「小張,這位有可能是把我當成了其他人吧,不要這麼無禮。」
當年,我就覺得這個研究員明明犯了事還沒被怎麼處罰有些奇怪。
現在,我明白了,他不僅身后有人,還狡猾精明。
五年時間,足夠他把那些卑劣的行跡給洗刷。
「不過,這位小姐,如果您還想鬧事,那我只能很苦惱地將您給『請』出去了。」
臺上的人,故作一副苦惱的樣子。
而他的學生,已然拽著我手臂,拉住我。
那人還故意把我往地上的玻璃碎片上拽。
就在我重心不穩,要摔倒在一片碎渣上時。
一只骨節分明的手伸出來,輕摟住了我的腰。
「王和,你還真敢讓你學生對我學生動手啊?」
……
我曾經在夢里夢到過很多次和他重逢時的場景。
卻沒想到,會是這樣——
……
我發怔地盯著男人的側臉,摟著我腰間的掌心溫熱,好像在一遍遍提醒我他是個活人一般。
臺上的男人,已然如同活見鬼般連連后退。
可不是嗎。
我們親眼看著他下葬的秦自牧,讓我遍遍魂牽夢縈的秦自牧,就站在我的身側。
高挺的鼻梁,金絲邊框眼鏡。
ADVERTISEMENT
臺上的男人已然慌忙,倒不如說,大驚失色。
我張了張口,想喊出的名字,卻因為太久而忘記發音。
這世間,好像太過荒誕了。
……
會場進入自由討論的時間。
剛剛那場鬧劇,也因為講臺上的人以身體不適為由退出而陷入暫停。
「還要牽著我的手到什麼時候?」
身旁的人,好整以暇地望著我。
他依舊穿著藏青色的風衣,薄薄的鏡片擋住一汪深邃的眼。
溫柔,有風度。
我下意識地松開了握著他手腕的手,然后又緊緊抓住。
我抿了抿唇,拉著他,往酒店的會場外走。
……
我步履匆匆,身旁人流竄動,所以手心那點溫度便格外滾燙。
直到,把他拉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
男人比我要高一點,插著口袋,垂眸看我。
好像多年前,他也是這麼平靜地望著我。
我深深吸了口氣。
抬眼,看他。
「別鬧了,段楓。」
「……」
他就這麼看著我,一秒,兩秒。
然后笑了。
「啊,第一次裝,好像不太像?」
「……」
其實還挺像的,因為不止我,連那個講臺上的人都大驚失色。
可秦自牧都成灰了,灰不可能再變成人,這是堅定的唯物主義者在下一秒反應過來的事。
我抬手,輕輕蹭了蹭他的眼尾。
「把痣遮掉,就更像了。」
他笑得惡劣。
「我故意留的。」
「……」
我把段楓當替身這件事,讓段楓知道了。
「很失望嗎?我不是他。」
男人伸手,摸了摸我的頭發,出聲問我。
我搖了搖頭。
「沒有,他如果真活了,我會更難受。」
以前研究所里的朋友見我消沉成那樣時,曾經出聲告誡過我,秦自牧不會想看我變成這樣。
那時的我,紅著眼眶,已然到了崩潰的邊沿。
ADVERTISEMENT
「不想看到這樣的我?」
「那就讓他活過來親口跟我說啊?」
……
現在想想,無非就是偏執近絕望的希冀。
想把他氣活過來,想讓他出現在我面前,
哪怕是無奈地勸解我也好。
哪怕是失望地責罵我也好。
我猛地,被人摟在了懷里。
近距離接觸時,才能發現段楓和秦自牧的不一樣。
一個是永無止境粘稠的黑夜,一個是天方夜譚般的高蓮。
「婷,我現在才明白。」
「你永遠也不會因為我和別的女人互動而生氣,你只在乎我的臉。」
「我不要你的愛了。」
「我要你的眼睛。」
「你看著你心上人動情的眼睛。」
他輕吻過我的脖頸,熱烈而戲謔。
「我愛你。」
「但你不配高尚的人,所以你該跟我在一起。」
面前的人張開雙臂,擁抱我。
「跟我一起到地獄里去吧。」
「那才是我們這樣人的歸宿。」
最后一句話,恍如囈語。
11
我和段楓的婚禮,將在下周六舉行。
我不覺得跟他結婚有什麼不好。
他就算滿身瘡痍,就算是從內里腐爛開,只要他的臉沒有被刮花,我就愿意待在他身邊。
有的時候我覺得,我的執念已經到了瘋狂的地步。
深入骨髓的想念,我迫不及待地渴望和某個人相關的東西。
閨蜜知道我的事情后,略有些憐惜地看著我。
「婷,你該去看心理醫生了。」
……心理醫生會約的,但大概是在我結完婚之后。
婚禮的會場就布置在市里最好的酒店,有一點不得不說,段楓對婚禮還是蠻用心的。
就連婚紗,都是我一件件穿上,跟木偶一樣任人擺動,然后他親自挑的。
巨大的妝鏡前,我看著鏡子里的自己。
好久沒有這樣盛裝過了。
我也好久沒見過這樣精致的自己了。
忽然有人,從身后摟住我。
我和他一同,看著鏡子里的我們。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