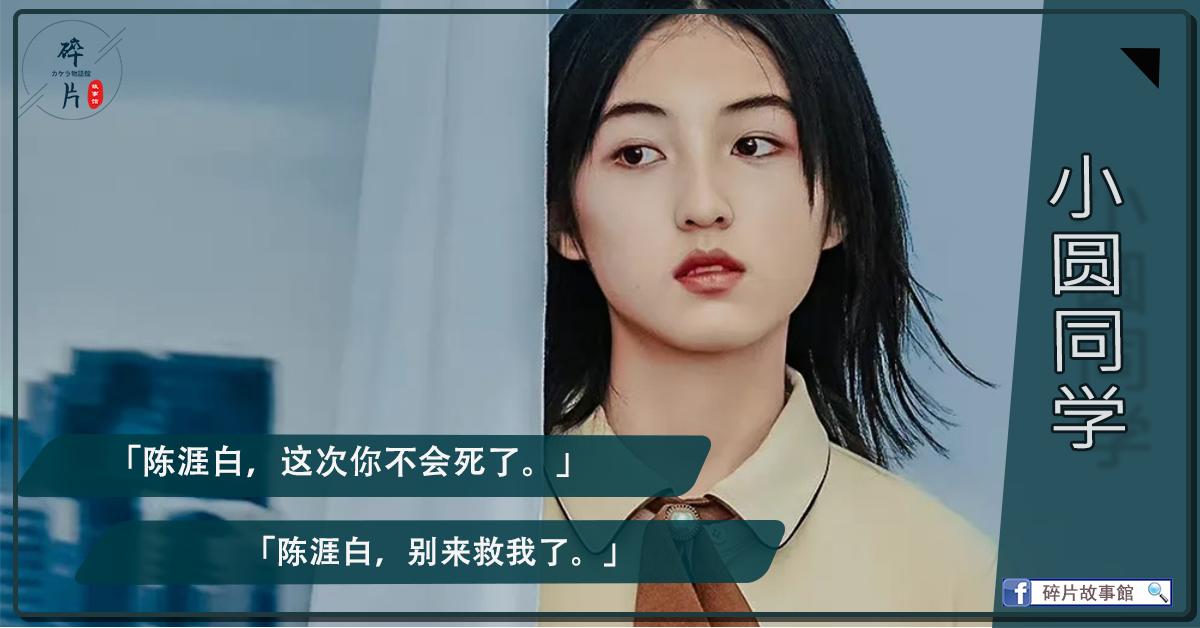《小圓同學》第7章
我至今不知道陳涯白是怎麼樣進來的,他像是一個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英雄。
樓很高,不可能跳下去。他就把我和阿花托舉在窗外,自己站在著火的房間里面。火光從背后照亮他的眉眼。我聞見皮肉燒焦的味道。
我赤足踏在樓外的一點凸起中,陳涯白一直等到窗外有消防隊員通過救援設備上來,親眼看著消防員把我和阿花接穩的時候,才轟然松開手。
我沒想到,第一次夢見他,就是這樣讓人難過、記一輩子的生離死別之景。
夢中的我被消防隊員親手接過去,并沒有和現實里發生時一樣嚎啕大哭,只是安靜地看著他,我說:「陳涯白,這次你不會死了。」
他的眉眼都是痛楚,終于支撐不住往后面倒下。
我最后說:「陳涯白,別來救我了。」你要自己,自己走到你的未來去。
我的未來沒有你,一片昏暗。但你的未來要是沒有我,那真是一片坦蕩。
我一出生就被說是小掃把星,我媽因懷孕下崗,從此事業再沒起來過。我爸那年開始陸陸續續生病,我是一切失意的來源。
從大火的夢之中驚醒后,我渾身是汗,摸索著打開臺燈,看了看信紙。我腦中的回憶每一瞬都在更新,這次真的是只屬于我自己的黑暗五月了。
那天受難的夜晚我沒有給他打電話,一個人扶著墻壁在黑暗之中行走,沒人再給我撐腰。我媽也有點自責,但不多。已經匆匆趕回來,秘密地給我辦了轉學手續了,預備在六月就離開。
可我也不是太能吃虧,忍氣吞聲的人,先是捅了林隨一刀;后是把他所做之事捅到了他的學校,我知道林隨最大的驕傲就是他的學校,我痛了,那麼他也該痛一痛。
ADVERTISEMENT
只是因為這次各方勸導的緣故,因為沒有人支持的緣故,我能做的、我敢做的也只有這麼多了。
這件事在我們那無聲無息,叔叔嬸嬸都捂得嚴嚴實實的。在同學眼里,我不過是因病請假了半個月而已。
重新再看這張和十七歲的時空相連的信紙,我很慶幸這回沒再拉陳涯白下水,我至今都忘不了當初陳涯白把林隨打得半死之后,他媽媽流著淚問他的那句話:「涯白,你是要當警察的人,怎麼能留下和流氓一樣打架斗毆的案底呢?」
我沒有立場為他說話,只能在拐角處捂著嘴哭泣。
好在我改變了這回的經過,我一個人就夠了。信紙上陳涯白已經很少說話,他在一個午后曾經潦草寫下,「小圓同學怎麼請假了半個月,我才發現她很久沒來了。」
我忍了很久的眼淚,才故作輕松地回答他:「她隔壁市的表姐結婚了,她得當伴娘,就過去幫忙婚禮籌辦了。」
陳涯白沉默了一會,隨意地落筆應承:「婚禮啊。」
話題就此結束。不知陳涯白是否記得,我們的談話從他問未來的他是否和小圓同學結婚開始,到現在的他對小圓終于不大關心結束。十七歲的陳涯白,只需要一點引導,就能回到他的路上去。
14
我一直緊張地算著日期,那邊 2017 年 6 月 5 號的日子被我一直牽掛在心里。雖然我知道可能那場大火不會再發生了,陳涯白也壓根不會去小圓同學的家。
因為原本會發生火災的那天晚上,剛好是校園文藝晚會。
陳涯白準備的鋼琴獨奏《起風了》正在節目單中,他不可能離場。
ADVERTISEMENT
可我還是焦灼難安,像是黎明之前的黑夜,十分難捱。
我主動在信紙上落筆,小心翼翼地寫字,故作不經意道:「教母來問一句,你的節目準備得不錯了吧?會上場的吧?」
等了很久才等到回音:「當然,練了那麼久,不上場不是白費功夫嗎?」
我放下心,平靜地接受陳涯白愿意上場并非因為小圓同學緣故的事實,他只是因為不愿浪費時間白費功夫。他甚至沒有問我,為什麼小圓同學沒有來。
這一天,我請了一天的假,安靜地待在家中,窗門大開,白色的紗被夜風吹動。我安靜地等待自己的結局,死亡或者被陳涯白遺忘。這兩種結局其實對我都差不多,但是我是真的很高興。
陳涯白,我比誰都希望看見你活著,永遠都在陽光之下的。
我靠著沙發,卻突然睡著了,像是陷入了時間的漩渦。
我又做夢了,也許這次不是夢,是真的仍然發生的事情。
我看見夢中大火重新在我家里燃起,我不知所措,身旁再沒有那只阿花。我絕望慟哭,卻被一個干凈的懷抱給抱住。他這次再沒有和我交集,對十七歲的小圓同學來說,陳涯白只是一個有些陌生的同班同學。
但他還是來了,陳涯白把我托舉到窗外,身上不再是藍白色的校服,而是預備節目時穿的黑色西裝。
而熱風滾燙,他坦坦蕩蕩,忍受痛苦還在微笑,他說:「小圓同學,你別害怕,消防救援很快就到了。」
他說:「有個人一直阻擋我來見你,我可是越過她的阻礙來的。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