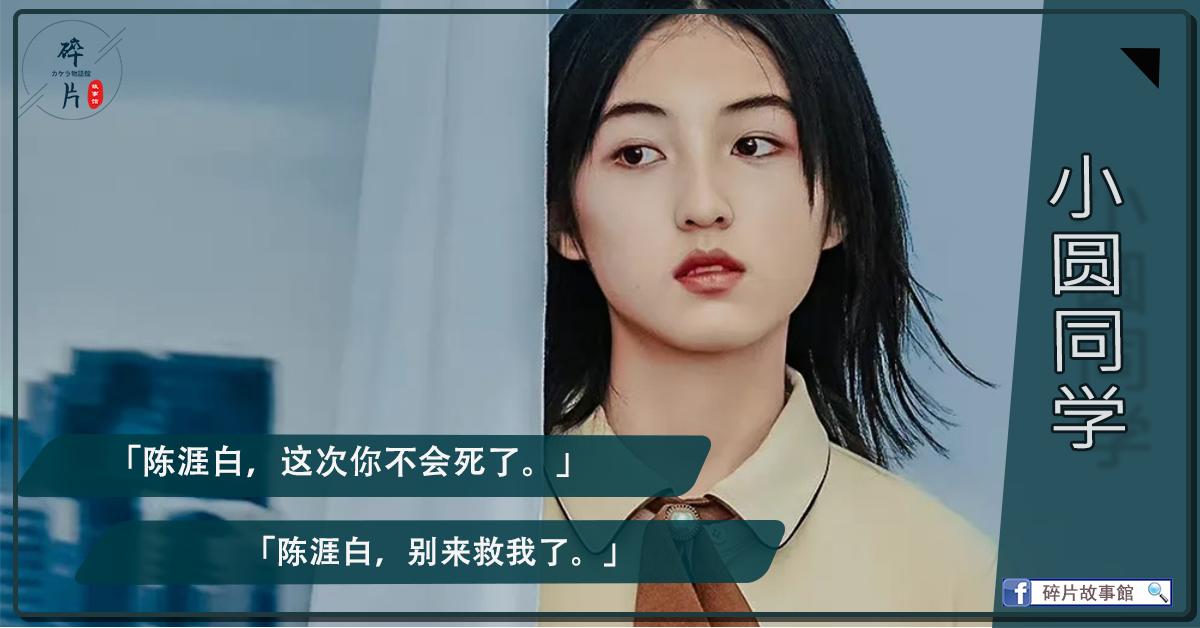《小圓同學》第6章
你不會和別人說的,對嗎?」他松開手,掌心都是從我頭上扯下來的頭發,「畢竟,沒人會相信你,會管你。」
我打電話給我爸媽,果真如他所料。他們要息事寧人,替我轉校,離開這個地方,替我掩住這羞恥的罪過。
我在夜里,打通了那個電話,帶著哭腔道:「陳涯白,幫幫我。」
放下電話的時候,我顫著指尖,卻從事發到現在一滴眼淚都沒掉過,眼淚只會讓他們覺得我軟弱好拿捏,可是從陳涯白出現在我面前的那一刻起,我嚎啕大哭。
陳涯白,我好疼啊。
我后來再沒見過他那樣的人,還穿著藍白色的校服,俯下身來抱住我,幾乎是在用全身的氣力抱住我,可動作卻又那麼輕柔。他把我拉起來,帶我去醫院,帶我去報警,去打林隨,他和我都不要息事寧人。
他替我在求公道。
學校里那時候也知道我的事情,有男生會在我經過時發出古怪的笑聲,江子舒和她的朋友會用憐憫的眼神看我。陳涯白在校內從不違紀,卻不知為何在球場上和對面男生起了沖突,聽說籃球都砸人腦袋上了,腦袋縫了好幾針。江子舒也在一個午后面色難看、低聲下氣地來和我道歉,說不該把我的事情在學校里傳出風聲的。
從此學校里再沒人敢議論紛紛。
唯有我路過年級辦公室時,看見陳涯白媽媽流淚問陳涯白,為什麼要這樣。
陳涯白沒說話,不經意地抬起眼,和在門口的我對上視線。
他沒說話。我也是。
他從黎明走來,救我于混沌之中。
12
我已經三十歲了,但我永遠會記得他,記得十七歲的陳涯白。
ADVERTISEMENT
我記得他怎樣把林隨摁在地上打,眉梢都是狠絕之意,巡街的警察趕到才能把陳涯白扯開;也曾看見他升起紅旗,仰望天空,眉眼懶散地沐浴著陽光。他是可以一直往上走的人,熱烈、明朗、清澈。
我把林隨的事情捅到他的學校了,原來他是因為廁所偷拍等惡性事件才不得不休學在家的。但是我們這邊的人都不知道,還以為他是那個高不可攀的名校學子,嬸嬸一直替他小心地隱瞞著,從小到大,她都把他寵得像寶。
我借住在他們家的那段時間,他們未必不知道林隨的齷齪心思,縱容和無視才是最大的幫兇。
也許從一開始,我就是目標,他們欺負我身后無人可依,以為我只是一個可以隨意拿捏的小女孩。可有人給我撐腰的。
我們把醫院的檢查報告和警局的立案單都拷貝發送給了學校,林隨的學籍被學校徹底開除了。本地電視臺媒體對林隨的犯罪行為進行了報道,他外在溫和的皮囊被撕下,其中乃是一顆黑色的獸心。
叔叔嬸嬸再也不敢罵我不知廉恥,因他們連家門都不敢邁出去一步。我媽曾嘆息說:「林遇安,差不多得了。別太過火,女孩子家的,這種事傳遠了還怎麼生活?家丑不可外揚。」
我沉默了很久,說:「我有什麼錯?」
這是陳涯白那天和我說的。我沒有錯,我是受害者,有人拉著我在尋求公正的路上行走,僅此而已。
表哥林隨在被押入警車的時候,曾回過頭看在人群中冷冷注視他的我和陳涯白,很輕地笑了一下,幾近毛骨悚然。
ADVERTISEMENT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這個笑是什麼意思。
我的表哥一直是個很聰明的人,高中物化理科一向逼近滿分,才能考入人人艷羨的大學,所修的專業與電路有關。六月份的時候,萬事皆平,蟬聲開始鳴起,我以為我要和陳涯白共同邁入一個盛大的夏天。
卻遭遇了一場由電路失火引發的火災。
我從林隨家搬出來之后,就住在原來我爸的老房子里。
我媽想要陪我,可我一看見她一開一合嘆息擔憂的嘴就心煩,最后還是我一個人住的。陳涯白經常放學會來找我寫作業,街角賣西瓜果飲的店主很喜歡他,每次都會順上兩杯西瓜汁給我。
有一次,陳涯白把藏在背后的手伸出來,掌心捧著一只黃色的小貓,迷茫地看著我。他說路上撿的,看我閑得發慌,就給我帶來了。這只小貓,他給它取名叫阿花。
我想了想,問:「陳涯白,你是不是怕我抑郁癥啊?」
陳涯白撐著眉角一直笑,肩膀發抖,他說:「不是,我是怕沒有合適的理由來找你。」
我怔住,和他同時別過頭去,余光里看見他耳尖和窗臺里正落下的粉霞一個顏色。
13
信紙那邊的時間已經到五月份了,我腦中關于十七歲的陳涯白的記憶不斷減少。連早已老死的阿花都沒有了在我身邊生活的痕跡。
三十歲的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了我十七歲的那場大火,發生在 2017 年 6 月 5 號。
陳涯白終于舍得來我的夢里了,幸運的是夢中的我還是十七歲的模樣,不像現在眉眼那麼黯淡。
我不知道從哪里開始起火,從夢中被嗆醒的時候已無逃生可能,房中已被火勢覆蓋,空氣炙熱到扭曲,小貓阿花就在我旁邊焦急地推我。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