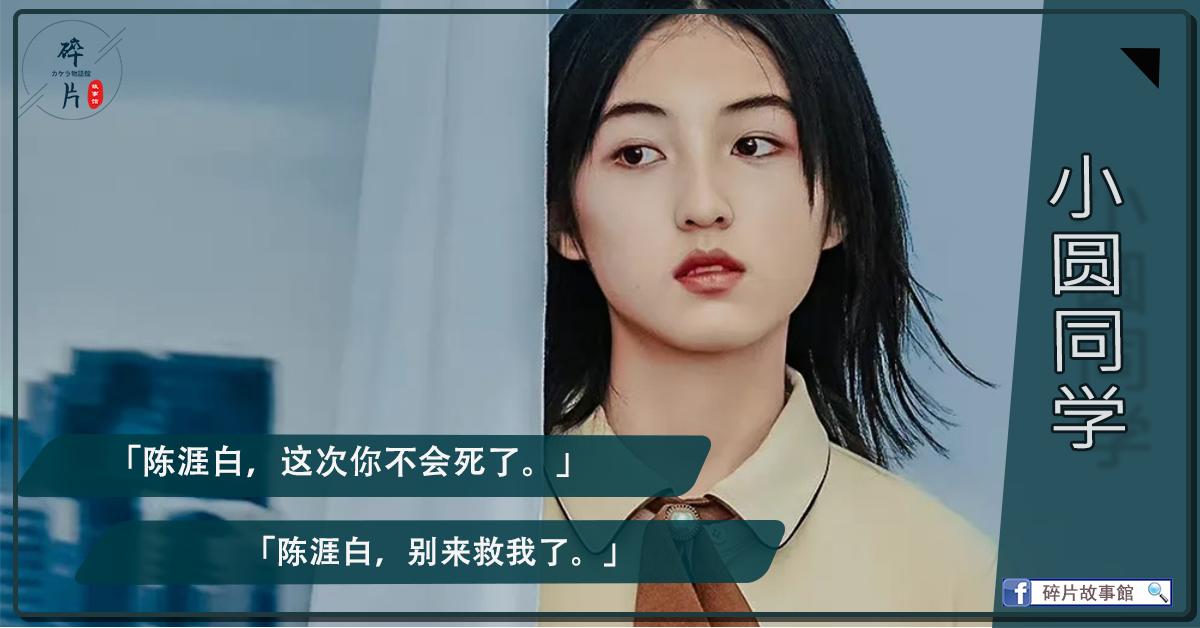《小圓同學》第5章
陳涯白是我唯一的、特別的朋友,很煩,但都在忍受范圍之內。他打球之前,他會強迫我坐在第一排,故意把外套蓋在我的發頂,一股干凈的皂香味。他個子高,在人群中很顯眼,身邊又總是有不少人,卻總是喜歡在外面隔著很遠喊我一聲小圓,以彰顯他的特別。
我開始查閱那所傳媒大學的資料,電腦上的網頁卻久久停留在它旁邊的那所警校的圖片上。
他的青梅竹馬江子舒曾經來找過我,警告我道,「陳涯白只是覺得你很可憐。他朋友多,對誰都很好,你別多想。」
我聳聳肩,如果不是她說,我壓根沒往那邊想過。
這些都是那年四月份發生的事情,漂亮得像是春天飄飛的柳絮。
10
但三十歲的我,只希望陳涯白過得順遂一點。那麼改變這四月份僅存的美好記憶也是值得的。
在我的提示下,信紙連接那端的時空里,陳涯白開始練那首歌,不得不因為諸多原因和江子舒接觸,年級里逐漸傳起來關于他倆的流言。
陳涯白和我表示不滿的時候,我正在和上次的相親對象吃飯。他坐在我對面,吃烤肉吃得滿嘴油光。
我把信紙掩起來一角放在旁邊,說不上來我為什麼要隨身攜帶這封情書,也許是真的不想錯過他的只言片語。陳涯白煩躁地寫:「年級里傳我和江子舒的閑話,我覺得小圓聽了會不開心。」
我咬著筆頭回他:「可是江子舒很漂亮不是嗎?喜歡江子舒會輕松很多。」
那邊停滯了很久,出現的字跡幾近平靜:「你希望我喜歡江子舒嗎?」
ADVERTISEMENT
我打了勾表示贊同。
相親對象席卷了桌上食物之后,終于抬頭看我疑惑地問:「你在寫寫畫畫什麼?」
我應付說是單位的事情。他不滿地嘟囔了一聲,狀似無意問道:「你們那的彩禮是多少啊?」
我的答案脫口而出:「一輛摩托車。」
話說出口,不僅是他,連我都愣住了,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說摩托車三個字,尋遍我的記憶也找不到相關的信息,我最終只當作是口誤。沒想到相親對象挺高興的,也許在他眼里,摩托車比八萬八的彩禮便宜不少。
我低頭,下意識地看向信紙,新的字跡已經安靜地在那里躺了很久,十七歲的陳涯白問:「未來的小圓開心嗎?」
其實陳涯白除了第一次得到他滿意的答案之后,再也沒有探尋過他和小圓的未來,按他的話來說就是,他會自己走到小圓的未來去。
三十歲的我回答他:「她很開心。」
她很開心,能夠穿越時空和你再次相遇。
11
陳涯白和江子舒越走越近,人人都覺得他們理所當然地在一起。
陳涯白已經不和我多說小圓的事情,他打球時再沒有小圓同學的專屬位置,再沒有給小圓指點江山該上哪個大學,他也再也沒有經常煩過小圓同學。
他的字越寫越少,像是對紙上莫名出現的仙女教母終于厭倦了一樣。這張信紙挺特別的,攏共就這麼大一張,寫滿了就自動翻新掉字跡,成為了嶄新的一張蒼白信紙,但陳涯白最初落下去的那一句:「小圓同學,我喜歡你,你不要不識抬舉」
ADVERTISEMENT
始終在第一行。
可是,我匆匆地掃了一眼新的對話記錄,滿紙出現最多的,是江子舒的名字。
「江子舒和我媽告狀,說我總是欺負同學,拜托我只欺負小圓。」
「江子舒很煩,我問她女孩子喜歡什麼,她把自己的購物車付款鏈接發過來了。」
「我練琴的時候,江子舒非要跟著,趕都趕不走。」
17 年的四月份很快就過去了,陳涯白因為六月份的校慶活動越發忙碌,那首起風了幾乎爛熟于心。在我的干涉下,陳涯白和十七歲的小圓同學終于沒和當初一樣熟絡,反而生疏了不少,像是兩條短暫交錯的線逐漸回歸到了平行。
五月份到來,我把 17 年五月份稱為我人生最黑暗的一個月。
人是會故意忘記讓自己感到痛苦的記憶的,我也不例外。
我的表哥,林隨,是個人渣。
我的嬸嬸瘋狂地罵我是個不知廉恥的女孩,她的兒子可是名牌大學生怎麼可能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一定是我主動的。叔叔紅著眼勸我,說親戚一場,表哥從小對我也不錯,他只是喝多了酒。
我爸趕回來抽了一地的煙,和我媽達成一致,最終的回答是:「遇安,算了吧,女孩子要名聲的。」
你的名字,就是隨遇而安。這樣的事情,就也忍了吧。
只有陳涯白問我:「你有什麼錯?」
表哥經常會進我房間,美其名曰輔導作業,然后我的內衣開始丟失。
我給媽媽打過電話,她說是我該改改自己丟三落四的毛病啦。
他替叔叔接我上下學,學校到家的距離有段黑巷子。在五月份逐漸開始有夏天氣息的一個夜晚,他就壓著我在骯臟的陰影里。
不知道過了多久,他放開我,我痛得蹲在地上。林隨蹲下身,柔聲道:「遇安,我只是喝多了酒。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