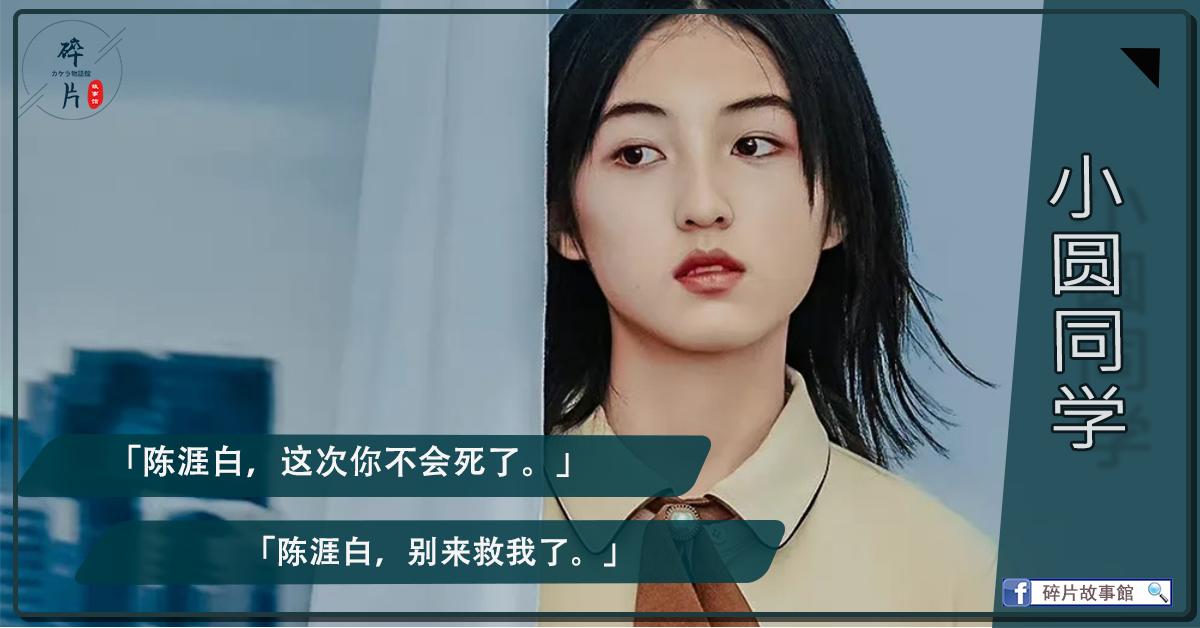《小圓同學》第4章
摩托車一路駛過繁雜的市區,往遙遠的海灣區駛去。已經是天空深藍的晚上,海灣區車少,他的速度就愈發快,只有海風能追上我們。
中途下了大雨,打在我倆的衣服上,順著頭盔往里頭滴落。濕透的衣服黏在一起,只有他的體溫是滾燙的。
那是我第一次不那麼討厭陳涯白。
他暢快地大笑:「帶你出逃。」
如果不是這場大雨,我不會把他當成朋友,允許他接近的。
8
信紙那邊的時間到了日記上的 3 月 31 日下大雨這天,我還沒找上陳涯白,他先找上我了,筆跡散漫:「在嗎?十塊錢替我算一卦。」
我心平氣和:「我是西方的教母,不是學道的。陳涯白。」
他無所謂地在我清秀的字體上畫畫,有點心不在焉。
我妥協:「好吧,算什麼?」
「算一算,我找到她的概率有多大。」
我有點不知所云,對面像是不滿意我的笨拙,我都能想象到他嘖一聲的樣子:「現在才中午,她剛剛急匆匆地就回家了,連書包都沒拿,看她沒做到這麼多的作業我會很難受。所以我打算翹課給她送作業。」
我替十七歲的林遇安謝謝你的熱心。
他輕描淡寫:「就是不知道她住在哪里,邊上同學都不知道。只知道她每次會做一路公交車,那條路上老小區挺多的,只能一個個找了。」
我滯住,我從不知曉原來他是這樣出現在我面前的,那時候已經是晚上了,難怪他說自己運氣不錯。
「我剛剛幫你算了一卦,往城東那條青春南路走,你會看見她的。」
他半信半疑:「真的?」其實我家住城西,青春南路在城東,他逛遍都不會遇見我。
ADVERTISEMENT
陳涯白,我幫你算了一卦,這一次你不會再找到她。
我有點心虛,但怕他看出來,寫得又快又穩:「真的。我什麼時候騙過你啊。」
我盯著信紙很久,再也沒有新的字跡出現。看來是信了。一股困倦涌上來,我上床就睡覺了。夢里浮沉浮沉,新的回憶替代出來,舊的記憶從我的腦海里一點點被擦掉。
那天夜里,2017 年 3 月 31 日的夜里,我沒能等到陳涯白,我坐在那個沙發上,聽著爭執聲,看見了遲來的一場暴雨。
陳涯白在青春南路上反復逡巡,遭遇了一場暴雨,沒找到他的姑娘。
9
我起床的時候感覺好累,記憶有一點空蕩,日記本還攤在桌子上。
「2017 年 3 月 31 日大雨。」只有日期和天氣,日記的主體卻是空白一片,像是被擦掉一截。
信紙上咬牙切齒多了控訴我的一句話:「你算的什麼卦,我在那條路上根本沒看見她。」
我嘆氣:「東西方文化有差異,算卦也許不是仙女教母的特長。下次給你搞預言術,你沒給她送成作業她應該還挺高興的。」
陳涯白不說話了。
我笑嘻嘻地寫字:「你別生氣呀,我告訴你一個小圓同學的秘密。她很喜歡起風了那首歌,她后來說要是你要是在六月份的校園文藝晚會上彈唱這首歌,她一定立馬愛上你。」
我看見那個「愛」字下頭洇出了墨跡,有人握筆在那處久久停駐,才恍然回神飛揚兩個字:「等著。」
學校琴房的鑰匙都在 A 班的江子舒手里捏著,作為學生會文藝部部長,她還管校園文藝晚會的事宜,如果陳涯白這次還是要練琴,少不了要和她接觸的。
ADVERTISEMENT
江子舒漂亮、優秀,最重要的是她和陳涯白算半個青梅竹馬,很喜歡他。
陳涯白死后,她不止一次來找過我,她揪住我的頭發歇斯底里,她問我,為什麼死的不是我。江子舒后來出國了,也許也是想忘掉陳涯白。
她和陳涯白才是一類人,我不是。
我感覺自己忘掉了一些事情,嘗試自己把記得的事情都給寫下來,普通的本子肯定不行,會像日記一樣被抹去字跡。我把那封情書的封皮拿來用了,我之前確認過,在封皮上寫字陳涯白不會收到。
從三月末那場大雨過后開始,我忘了因為什麼契機,覺得陳涯白其實還挺不錯的,不再抵觸他的接觸,姑且可以納入朋友的范圍內。我爸媽最終還是離婚了,我跟著爸爸,我媽從失敗婚姻解脫出來后迅速搬離了這座城市,我爸因為工作出差,那段時間把我丟給了叔叔家。
我抗議過,但他不管。
叔叔家有個表哥林隨,讀的名校大學,卻不知道怎麼休學在家,嬸嬸把他寵得像塊寶。我爸把我丟過來的時候,美其名曰,和我表哥好好學學,補補我那吊車尾的成績。
表哥開始給我補習,他戴著眼鏡,總是很溫和地笑。其實他比我爸媽都負責,甚至會接我上下學,他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陳涯白在校門口看到過他等我放學,扯著我的書包帶把我勾過去,一伸手就攬住了我的肩,很懶散地站著,一雙桃花眼卻瞇著看著林隨,親昵問我:「小圓同學,這誰啊?」
林隨扶了眼鏡,謙和笑道:「我是遇安的表哥,林隨。
」
陳涯白緊繃的脊背一下子松懈下來。
那時候,那件事情還沒有發生,展現的都是柔和的景象。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