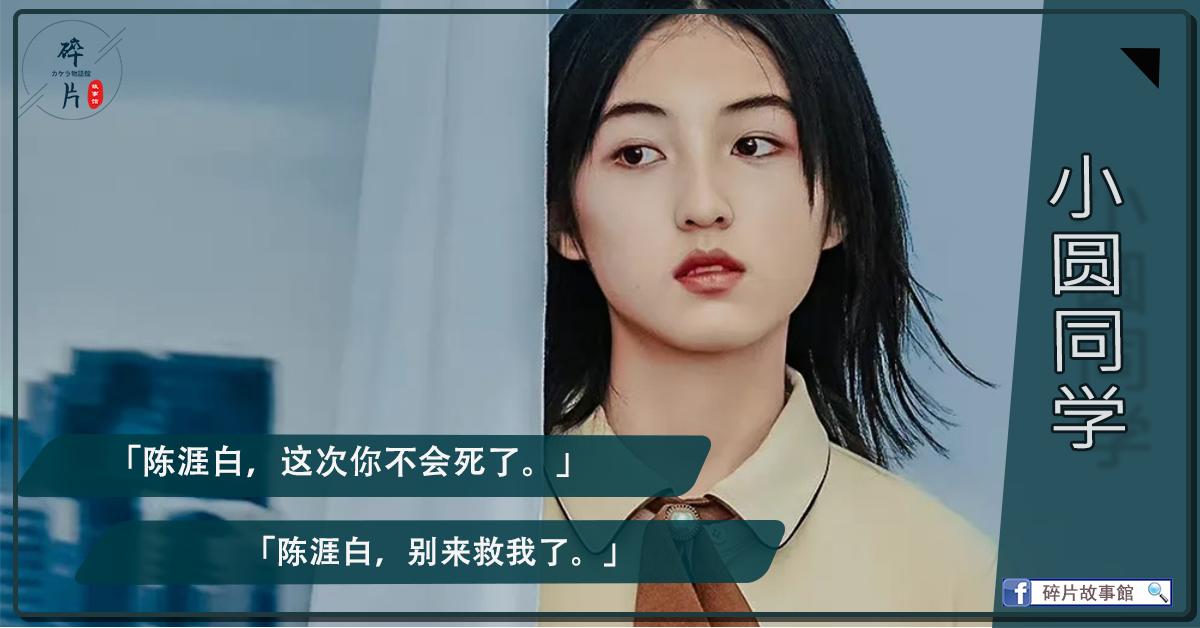《小圓同學》第3章
然后他在球場上虐殺了 A 班。
我安靜地聽著他的那些心事,只言片語之中好像重新看見了那個滿是藍白色校服的學校,我從不知道陳涯白的這些少男心事的。
我耐心地一遍遍糾正他的行為,不要太煩小圓,要保持距離感,太倒貼的男人沒人要的。
從小賣部回來不要給小圓順手帶草莓味的牛奶,給她帶提神的苦咖啡,作為好同學提醒她積極學習。
不要老是使喚小圓同學,來往要有禮貌地說你好和謝謝。
陳涯白按著我說的做了一段時間,態度對我好了許多:「她沒那麼討厭我了。」
我抿了抿唇,僵硬地寫道:「你覺得她很討厭你嗎?」
他沉默了一會,落筆:「是。」
我把頭沮喪地埋進胳膊里,無何奈何,因為我那時候,就是很討厭他啊。
其實陳涯白成績很好,他轉學來的時間晚,缺考了一門語文,其他科目都是逼近滿分,只是從前沒等到期末考試展露他真正的成績,導致我現在才知道。
我咬牙切齒,「那你期初考試干嘛要抄小圓的英語試卷?」
陳涯白筆跡散漫,意氣張揚:「不這樣怎麼能叫她小圓同學,誰都能叫她遇安,只有我從第一面見她開始,就是小圓同學。」
——我必須從一開始,就是特殊的。
他其實是個很耀眼的人。就算是我這種不關心周圍的人都知道,中學時候最奪目的人無非三種,家世容貌和成績,剛好陳涯白三樣都占了。他長得好看,父親是因公殉職的警察,至于成績排名吊車尾,也算是別出心裁的顯眼。
ADVERTISEMENT
不知道怎麼會喜歡我的。
我有點無奈,落筆涓涓:「為什麼一定是小圓呢?」
陳涯白回了四個字:「小圓效應。」
當丁達爾效應出現的時候,光就有了形狀。
而當小圓同學出現時,陳涯白的喜歡變成了具象。
7
「多少年的東西了,你知道我為了寄給你找了多久嗎?」我媽在電話那頭有點不耐煩,「上回不是答應了和那個公務員多見面的嗎?怎麼人說你不理他。」
我一手接著電話,一邊把媽媽剛寄來的快遞給拆開,隨口敷衍道:「很快就去見。」
電話被我掛斷,反蓋在桌子上。我知道電話那頭她必定已經生氣,然而我有更要緊的事情去做。
快遞里頭放了一個小餅干鐵盒,表面被火燒出黑色的痕跡已經在歲月里頭氧化,我屏住呼吸打開盒子,蒙滿灰塵的時光像潘多拉魔盒一樣打開。
里頭東西不多的,只有一本日記本,一只創可貼、一枚發卡。
我翻開日記本,其實我學生時代不喜歡寫日記,里頭的字跡少得可憐。我已經翻到我要找的東西了。
「2017 年 3 月 31 日海灣下大雨,和陳涯白奔逃。」
其實十多年過去,很多當時以為能記一輩子的場景,不需要三五年就會忘得一干二凈。但是我閉上眼,竟然還記得非常清楚。
我是一個沒人要的小孩,我很早就朦朦朧朧地意識到,我厭惡一切耀眼的人,包括煩人的陳涯白,因為他們看上去那麼值得被愛。那天是周五,我比放學時間要早很多地回家。
因為我爸媽最終一錘落定離婚,反而我心上的石頭落了下來,但是他們誰都不要我。
ADVERTISEMENT
我靠在沙發上,聽著爸媽推諉來推諉去,我爸說女孩得跟媽媽比較方便,我媽說不行她經濟條件不好。
門開著,街坊鄰居豎著耳朵在聽熱鬧。
我當時想,怎麼還不下雨,下場雨淹死我得了。
我閉著眼睛數數,數三十秒睜開,或許會是不一樣的景象,這是陳涯白教我的方法。還沒到三十秒,突然有清冽的聲音突然響起來,不應該出現在這里的陳涯白就站在門口,他十分用力地踢了一腳門,哐當一聲,爭吵的聲音被嚇得戛然而止。他面色難看,說:「吵他媽呢?」
我爸媽愕然回過頭,看著這個背脊高大的男生一時間竟然說不出話來。
陳涯白一字一頓地說:「你們不要她,我要的。」
他上前兩步攥住我的手腕把我往外拉,一路逃離爭吵的家里、聽熱鬧的鄰居,我跟著他急促的腳步走,才發現他另一只手上拎了個白色的書包,拉鏈還沒拉好,露出里面滿滿當當的作業,后知后覺地意識到原來我忘帶書包回來了,他是來給我送作業的熱心同學。
沒想到撞上一出狗血家庭劇。
陳涯白很生氣,抿著唇不講話,額角都隱隱跳動著,但又像是在難過。
樓下就停著一輛線條流暢的摩托車,我多打量了兩眼,陳涯白卻在它面前停下,他沒問過我意見,就把一個粉色的頭盔往我頭上戴,我腦袋一沉,他手使勁在我圓圓的頭盔上往下按。看著我憨態的模樣,自己低笑了兩聲。
「小圓同學。我運氣不錯。」
「從現在開始,閉上眼三十秒,是海水的味道。
」
騙人,哪里的三十秒,明明好久的。
我以前從沒坐過摩托車,我坐在陳涯白的后邊,為了安全不得不抱緊他勁瘦的腰身。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