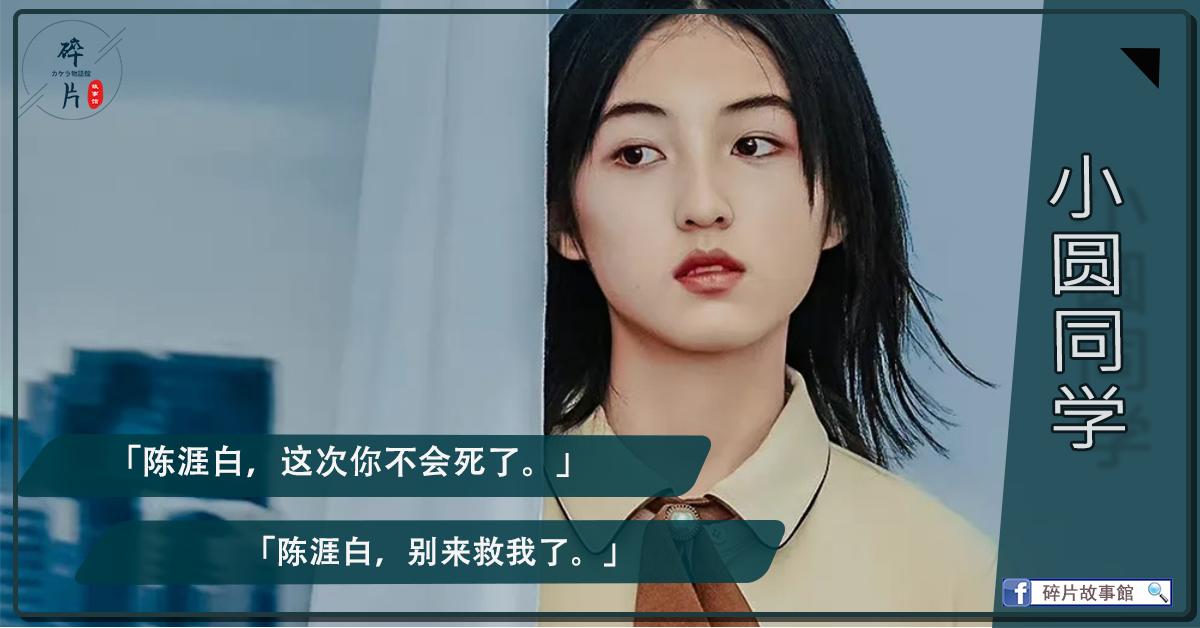《小圓同學》第2章
我還沒再繼續寫,紙上又出現了一句話,他問:「如果你是仙女的話,你在哪里?我怎麼沒看見你。」
我握緊了筆,寫得很慢:「我在很久后的未來等你。」
他慢吞吞地問:「小圓同學成為記者了嗎?」
我寫:「是。」
這是我撒的第一個謊。我的新聞理想在畢業第一年就死了,我在一個單位當文職,每天的任務是生產文字垃圾。
「我當警察了嗎?」
我寫:「是。」
第二個謊言。他沒走到他應有的未來。
他的筆跡幾乎壓抑不住欣喜,很久才鄭重又別扭地添上,狀似無意:「我和小圓同學,結婚了嗎?」
我的心轟然發燙,原來十七歲的他真的喜歡我,遺憾的是我三十歲才真的知道。我壓著酸澀,筆下的字幾乎在顫抖:「有。」
過了很久,幾行龍飛鳳舞的大字才得意地浮現出來:「早就看出來她對我有非分之想了。」
騙了個傻子,我真的愧疚。
4
17 年 3 月份,我因為成績大滑坡,在班主任辦公室外頭罰站。班主任給我爸媽打電話,沒一個在接的。
對面的墻上貼著各高校的招生照片,我漫無目的地讀過去。
我沒想過上什麼學校,當死則死,以后對我是摸不到的字眼。
耳邊突然出現陳涯白的聲音,他指著其中一張高校照片說:「我要去這個警校。」
他腿還瘸著呢,不知道在我旁邊站著干什麼。
我想偏過頭,他扣著我的后頸,不讓我亂動,指尖冰涼:「你得去我對面的傳媒大學,這樣過個馬路就到了。你當記者好了。」
我以為他看見了我上節課填的理想專業,要說什麼我的優點,比如實事求是敢于發聲之類的,陳涯白懶散地補充理由:「你笑得好看。
ADVERTISEMENT
」
廣播里在放那年很火的歌,好像叫《起風了》,我沒說話,突然沿著走廊往前走,走到拐角的時候,陳涯白突然笑著喊了我一聲:「小圓同學。」
我回過頭,他站在光的那一面,風把他的頭發吹動,側顏熠熠生輝。
他問:「你去干嘛。」
我沒好氣地回答:「上廁所。」
他看著我,含笑應了聲。
廣播里的詞正唱到「翻過歲月不同側臉/猝不及防闖入你的笑顏」,誰的十七歲遇見陳涯白,都挺煩的。
他出現一下子,眩暈我一輩子。
我后來去了那個傳媒大學,走過很多次那條馬路,閉上眼睛三十秒再睜開,都沒能遇見陳涯白。騙子。
所以,從一開始,就別相互煩惱了吧。
5
陳涯白的話其實不是很多,從上次知道他期望的答案之后,再也沒想起來我。
我把信紙夾在一眼就能看見的地方。幾天過去了,也沒見到新的字跡。直到我挨完五十歲禿頭領導的批評回來,下意識看向情書時,上頭終于有了新的字跡。
圓錐曼妙的曲線就出現在上頭,字跡散漫,帶了點不耐煩。
我磨牙:「陳涯白,你在仙女教母的情書上打數學作業草稿?」
他才恍然大悟:「你還在啊。」
對啊。我一直在。
我問:「小圓同學不理你了吧。」
信紙被摁下一個煩躁的印子。
看來說中了。
我看了一下日期,信紙兩邊時間流速是一樣的,那邊應該是七號,我生理期一直很穩定在七八號。
我說:「你今天不要去煩她。」
一個問號出現在我的字旁邊。
我解釋原因:「今天她生理期。」
然后我眼睜睜看著紙上的字劃了又改,最后只有一個顫著羞惱的哦。
ADVERTISEMENT
我忘了,現在他才十七歲,對于這些是會害羞的。
我放下筆,彎了眉眼。突然腦中卻閃過我從未經歷過的畫面,憑空出現,像是嶄新而確切發生過的事情。
我看見十七歲的林遇安走進教室,唇有點微微發白,課間人聲鼎沸,她看見自己桌子上多了杯溫熱的紅姜水。不知道誰放的。如果她轉頭,可以看見窗邊那個懶散少年用書蓋住臉,卻露出了發燙的耳尖。
這段回憶,開始變舊變老,不再清晰地封存在我的記憶里。
我眨眨眼,低頭怔怔地看著那張信紙,竟然想落淚,所以這是剛剛發生的嗎?因為我的字嗎?
我在情書上寫:「陳涯白,你從哪搞的紅姜水?」
他落筆:「別管。」
我話頭一轉,幾近哄騙:「仙女教母遠程而來,是替很久很久以后的小圓同學喊話,她說——高中的你太直男了。」
他沉默了。
我補充:「所以,你最好先聽我的指導。」
其實我根本沒抱期冀,陳涯白壓根不是會聽別人話的人,有時候自大得讓人發指。
但是他的回答是——好。如果能讓小圓同學更喜歡我一點的話,我的答案是,好。
我在辦公桌前,看著那行字,握筆的關節發白。
我之所行,跨越時光而來,欺騙我尚未長成的少年,教他如何遠離小圓。
不要再救小圓同學了,陳涯白。
6
陳涯白開始把我當他的廢話箱。經常以小圓為開頭,小圓為結束。他也會時常提起其他的事情,但很快又會繞回來。如果說,生命是一個循環往復的圓,那麼小圓就是他的節點。
「小圓新卡了個發卡,很好看。
」
所以他從小圓頭上順走了。
「A 班那個理科男又來找小圓借書,他自己不會買嗎?」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