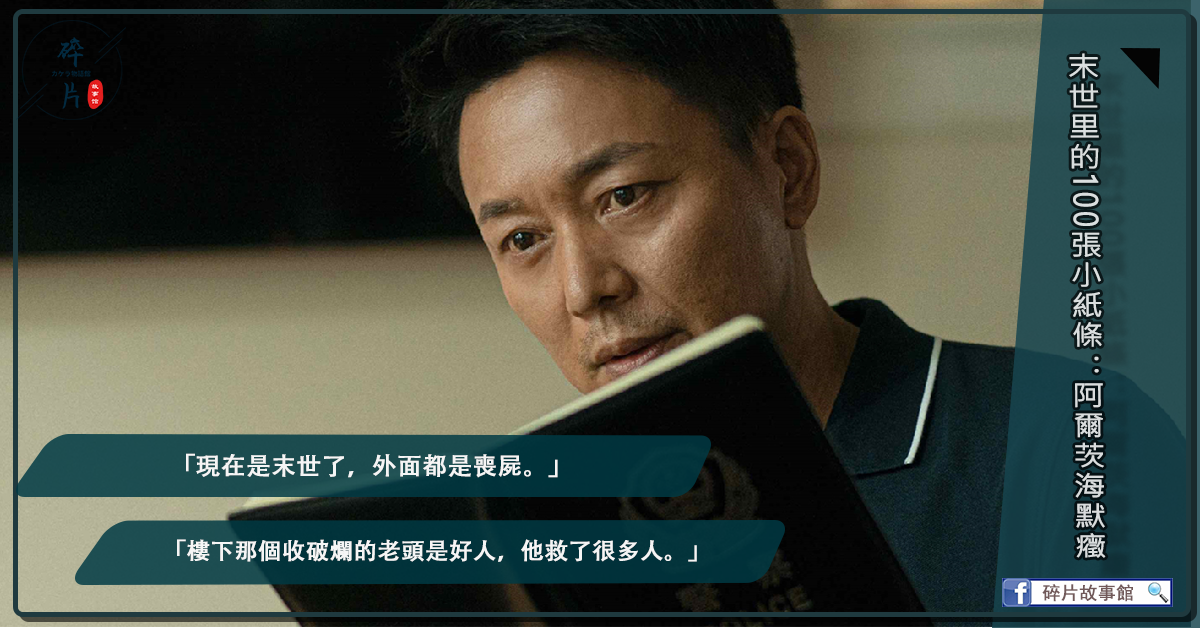《末世里的100張小紙條:阿爾茨海默癥》第9章
我馬上把開出租的工作辭了,專門留在家里陪老伴兒,為了找點事做,就在樓下擺了個三輪車,兼職收破爛。
其實,胡老師還不那麼糊涂的時候,就特別反對我干這個,她對我說:「你都這麼大歲數了,盡瞎折騰。」
我也懶得跟她吵,她這個人啊,哪兒都好,就有一條我受不了,矯情!可能是她在學校里訓學生習慣了,回家也老喜歡教育我,吵得我頭疼,不如到樓下擺三輪去。
不是我吹牛,要不是喪尸爆發了,我下象棋的水平,在小區里就要沖進前三了。
剛開始,胡老師狀態非常好,一點看不出記憶力減退的樣子,兒子媳婦也時常回來探望。可是后來,胡老師記性越來越差,連他們是誰都認不出來了。
今年中秋和國慶,他們也沒回來,我們在電話里大吵了一架,冷戰到現在。
「胡老師,待會兒我教你釣魚,學不學?」
「好啊好啊……」胡老師像個小孩一樣快樂。
我們開了三個多小時,這才抵達目的地。這個野生水庫,比我前幾年過來的時候還要荒涼,可以說是與世隔絕了,但風景非常漂亮。
我把房車停在草地上,又支起了帳篷。我翻出鐵鍬,帶著胡老師一起挖蚯蚓,然后手把手教她釣魚,晚上煎魚吃。看著胡老師開心的樣子,我也笑了。
去他媽的末日,世界毀滅跟我也沒關系了,我只要胡老師一個人活著。
7
然而,快樂只持續了幾周,胡老師就開始想家了。
「我們怎麼還不回家呀?」
「地震來了,房子倒了,我們以后就住這兒了。」我撒了個謊,這個時候,小區早就被喪尸占領了。
ADVERTISEMENT
「哦。」
可雪上加霜的是,可能由于胡老師在老房子里住習慣了,換了個新環境,反而開始不適應起來,連吃飯也不積極了。她坐在帳篷里,抱著膝蓋,看著水面發呆,一坐就是一整天。
我怕她寂寞,不停地陪她聊天。我從我們剛認識的時候開始說起,說部隊的事,一直說到我們倆結婚,說到兒子出生、上學、工作、結婚,說到教師節,當年的學生一個個回來看望她……
可是,不管我說得再多,胡老師始終是茫然的表情,好像我在說和她無關的事情。
一個月,兩個月,我眼睜睜地看著胡老師的病情一步步加重,從開始的說胡話,到一天都不開口說一句,然后臥床不起,大小便失禁,身體也變得僵直,吃藥都毫無用處。
我從來都沒這麼絕望過,看著老伴兒死在我面前,卻無能為力。
恍惚之間,我又開始了下一次循環。
原來,胡老師才是我內心的執念,只有老伴兒活下來,我才能擺脫這個無窮的時間循環。
8
還是11月7日,再次回到起點。
這一次,我既沒有組織小區的人,也沒有租房車逃離,因為我很清楚,這兩條路都行不通。
我熟練地去超市采購大量物資,全都搬進自己家里。同時,買來鋼板和鐵條,重新焊接、加固門窗。又去買了厚厚的窗簾,把客廳、臥室的窗戶全部裝上。
武器有點麻煩,現在刀具管制很嚴格,一時之間,我也不知道去哪里能搞到。至于槍械,那更不可能了,除非喪尸爆發之后,去公安局借幾把槍,但難度太高,這一路有去無回。
ADVERTISEMENT
思來想去,我還是翻出了家里收藏的那把老古董大刀。
根據我老爹的說法,這把大刀是1933年29路軍喜峰口戰役犧牲的老兵留下來的,老爹參加八路軍之后,一直隨身攜帶。后來老爹走了,這把刀就傳給了我,我又重新做了皮革刀鞘,保存至今。當年在文工團的時候,我就是靠著29路軍的無極刀法,被大家夸成文工團第一刀神。
「老家伙,當年靠你打鬼子,現在還是要指望你殺喪尸了。」
這把大刀已經銹跡斑斑,我用砂紙打磨了一遍,又用磨刀石重新開刃,再用麻繩綁住刀把,系上了紅布。
有了武器之后,我心里就有底了。
11月8日那天,當喪尸沖進小區的時候,我藏在窗簾后面,什麼也沒做。這一次,我絕大部分時間都守在胡老師身邊,悉心照料,只有缺物資的時候,才冒險出去。
最終,我們堅持到了兩個半月,這是目前為止時間最長的一次。
可是,讓我失望的是,胡老師的病情再次加重了。喪尸的爆發,似乎對她的精神也產生了負面影響。
一開始,胡老師還能自己穿衣服,漸漸地連衣服也不會穿了,她急躁地在屋子里走來走去,嘴里說著一些前言不搭后語的話,尿失禁的次數越來越頻繁。
看著老伴兒的病情一天天惡化,我幾宿幾宿地睡不著覺。
最終,我情緒也崩潰了,我握著刀下樓,大吼著沖進了喪尸群,大開殺戒,砍翻了數不清的喪尸,然后自己也被喪尸撲倒,失去了意識。
9
接下來的循環里,我陸續嘗試了許多種辦法,可無論我怎麼做,胡老師的病情都會惡化。
我的精神極為沮喪,這幾乎是一個無解的問題。
終于,在某一次循環里,我失去了所有希望,對胡老師說:「老糊涂,就這一次,我想靜一靜,你自己照顧好自己吧,不要怪我。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