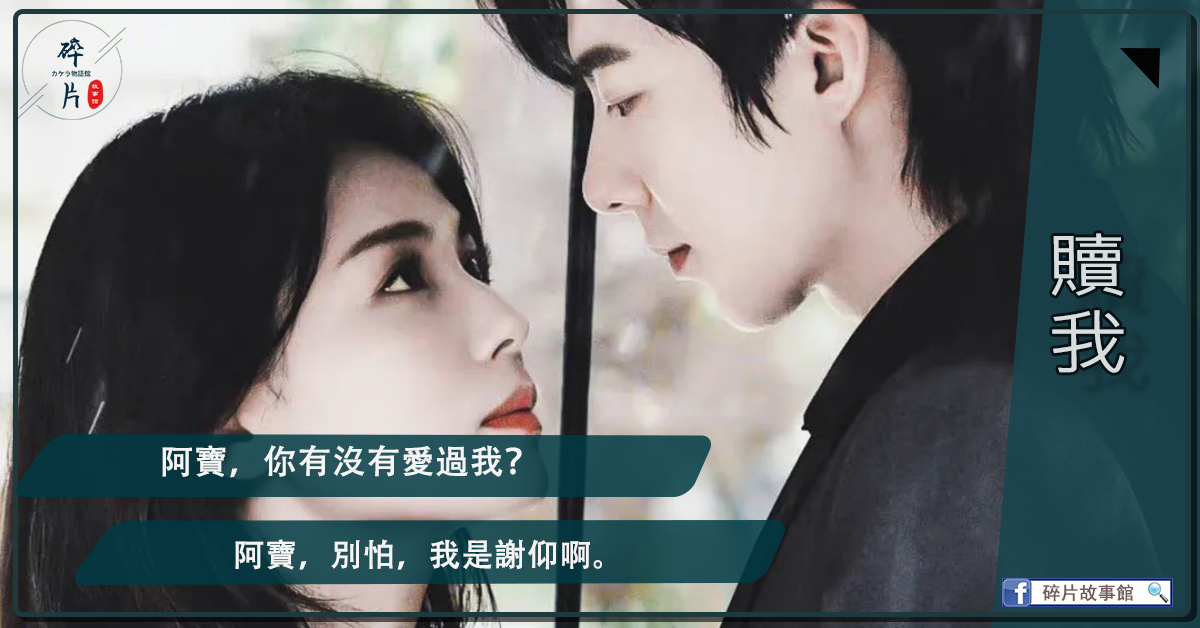《贖我》第7章
今天如果潘華不落網,那麼警方就會進行地毯式摸排,直到潘華被捉拿歸案。
「放下你手上的槍!你已經沒有退路了,不要做無謂掙扎和反抗!」
謝仰湊近我的耳朵,溫暖的呼吸打在耳畔:「阿寶,好像走不了了,你愿意陪我一起死嗎?」
耳鬢廝磨。
而我閉上了眼睛。
「謝仰,伏法吧。」
謝仰低笑,好似溫柔呢喃。
「我才不要,被抓了,你肯定不會再看我一眼。」
「與其從此陌路,不如一起去死好了。」
24.
謝仰扣動扳機的那一刻,我突然暴起,一手握住他的手腕,一手肘擊。
手腕翻轉。
槍聲響起。
槍口偏離了我的太陽穴,耳邊炸開巨大聲響。
然而子彈沒有打到我身上。
我沒有看到彈殼。
奪下槍的那一刻,我反身將槍口對準他。
但是手上槍的重量不對,我下了彈夾,彈夾中空無一物。
是把空槍。
他看我的眼神我看不懂。
太過復雜。
我來不及去思索他是什麼眼神,拔出我大腿上綁著的那把,謝仰昨晚給我防身的槍。
這把可是子彈滿膛。
即使成為敗寇,謝仰臉上也沒有什麼挫敗感,他仍然挺直如松柏。
向我伸出手腕。
「阿寶,抓我走吧。」
警察圍了上來,嚴緒拉住我。
「阿寶……」
我接過手銬:「沒事,讓我去。」
「也算是,給這五年正式畫上句號了。」
25.
謝仰又一次,在我面前被押上了警車。
路過我時,他停住了腳步。
「阿寶,別放松警惕,我哥是條毒蛇,他什麼事兒都能干出來。」
就在此時,嚴緒接到了電話,說發現了潘華的蹤跡。
在另一個能跨越國境線的地方,找到了潘華的棄車。
ADVERTISEMENT
「阿寶,你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去副駕駛待著,等會兒不要出來。」
謝仰突然湊過來,大長腿抵著車門死活不上車。
「把我也帶去,我才是最了解他的人。」
「你們也不想突然被蛇咬一口吧?」
嚴緒看向謝仰:「我們憑什麼相信你?」
謝仰臉上帶著幾分陰冷。
「他都捅我刀子了,我當然要捅回去。」
我皺了眉頭:「有你什麼事兒,車上待著去。」
嚴緒卻同意了。
「我們可以帶你去,但你必須在車上待著。」
「阿寶你也是,你留在車上看著他!」
26.
嚴緒帶著人下去檢查廢棄的面包車,我和謝仰在車上大眼瞪小眼。
謝仰湊過來親了我一口。
我一個擒拿手把他按在車門上。
「敢襲警?罪加一等!」
「罪加幾等都無所謂了。」
謝仰現在已經徹底擺爛了。
「阿寶,如果我能活下來,你還會要我嗎?」
我翻了個白眼:「我是警察,你有犯罪記錄,政審過不了,要我說多少遍?」
謝仰沉默著,突然笑得很欣喜。
過去的五年里,我沒見過多少次他真心笑的樣子。
最近反倒是越來越多了。
「那要是……」
我捏住他的嘴:「閉嘴。」
我在聽。
嘀嗒、嘀嗒、嘀嗒……
在沒當臥底之前,我曾經參與那起公交車爆炸案,深入前線,是那起案件的經歷者之一。
為此我在 ICU 躺了整整一年。
當了一年的植物人。
這種帶聲音的定時炸彈早八百年就被淘汰了,但是潘華用了。
一來是因為這種東西太久遠,可能拆除方法都沒人知道,但是容易制造和生產。
二來這種滴答滴答的聲音,可以給人制造巨大的精神壓力和恐懼。
這種聲音越來越急。
ADVERTISEMENT
嘀嗒嘀嗒嘀嗒……
聲音離得太近了。
我已經分辨不出炸彈是在哪里,但是我知道,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我拉著謝仰沖下車,一邊跑一邊對嚴緒他們喊道:「快跑——」
我的聲音淹沒在鋪天蓋地的爆炸聲中。
而這種爆炸聲,在我身后。
我只記得,在我失去意識之前,有人抱著我撲了出去。
27.
在我昏迷的時候,一直有人在我耳邊講述案件的進展。
我有時是清醒的,有意識,但眼皮沉重,好似有什麼東西困住了我。
潘華在一條漁船的貨倉中,躲在腥臭的魚蝦中,若非警方在掃尾的時候看到了那條停靠的漁船,也許他就真的逍遙法外了。
炸彈沒有安裝在廢棄的面包車上,而是被埋在面包車車轱轆壓過的地方,所以當警車停靠的時候,就會壓在炸彈上。
他講了很多東西。
我從潘華落網一直聽到潘華被判死刑立即執行。
我聽到了父母的抽泣。
聽到了嚴緒的碎碎念。
那謝仰呢?
謝仰去哪兒了?
我迫切地想要知道謝仰的消息,努力掙脫束縛,想從昏睡中醒來。
終于在秋日的清晨醒來。
我媽正提著護理包走進來,看著我睜開的雙眼,把包一扔就去叫醫生去了。
其實可以按一下鈴的。
醫生說醒過來了就沒什麼大問題了,剩下的傷只需要等它慢慢愈合。
很多人來看我,我一張口喉嚨嘶啞,他們便叫我不要說話,好好休養。
一直到嚴緒來看我。
「謝仰呢?」
我的聲音嘶啞得不像樣子,簡直都要聽不出來我說的是什麼。
嚴緒將手中的梨湯放在床頭桌上,拉了個凳子過來,喂我梨湯。
「失血過多,搶救無效死亡。」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有一瞬間我的雙眼模糊,我在心里告訴自己。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