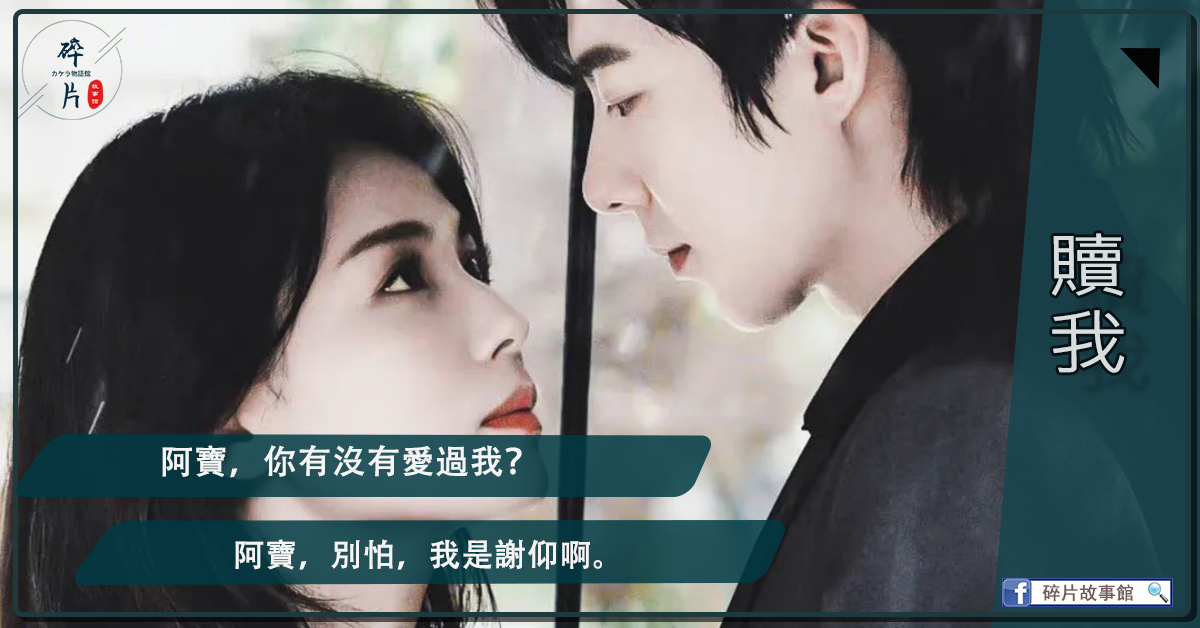《贖我》第6章
失策了。
看著面前兩個飽死鬼,我忘了問他們食堂在哪兒了。
沒辦法,只能自己去找食堂。
這里應該就是那個簡易的制毒工廠。
不過現在不是查看地形的時候。
誰知道潘華會不會設局等著我呢。
潘華殺我之心不死,要小心謹慎。
我從倉庫里走出來,一路上防守松懈。
好了,已經確定是個局了。
說不定潘華現在正在哪個角落看著我。
等我要有什麼動靜,就放冷槍給我一梭子。
此時,正在監控前站著的潘華,看到了那個女人,抓住自己手下的衣領逼問。
「食堂在哪里!快說!不說噶了你!」
……倒也不必如此坦蕩。
20.
謝仰回來的時候我正在食堂嗦面。
他風塵仆仆滿眼疲憊。
倦怠地靠在門上打哈欠。
「我累得要死,你還有閑心思吃面。」
我吹了吹剛出鍋的雞蛋面。
「又不是我讓你累的。」
一口面還沒戳到嘴里,就被謝仰截和搶走了。
他跟不怕燙銅牙鐵嘴似的,風卷殘云一整碗面下肚。
然后淡定地喝下最后一口面湯。
「有點咸,你不適合做飯,沒那個天賦。」
「幸好之前沒讓你給我做飯。」
是的,之前都是謝仰給我做飯的。
他做飯水平一般般,夠吃個家常。
又菜又愛做。
偏偏又有癮,在某一段時間每天都回來給我做飯,然后讓我點評手藝。
我都一概說好吃。
其實才怪,也就那樣,不咸不淡不出彩。
我餓得眼冒金星,氣得頭腦發昏。
我找到食堂的時候連鍋都洗得干干凈凈。
只能自己下一碗面。
「謝仰!」
我真想把他打得把吃下去的吐出來。
我掀了桌子直接跟他打起來了。
ADVERTISEMENT
用盡我在警校學到的一切,招招致命。
然而一個餓昏了的我怎麼打得過剛吃飽飯的謝仰?
沒幾招就被制住,兩手腕被他抓在手中。
「為了碗面至于嗎?我再去給你下一碗。」
真是說得風輕云淡。
我張嘴對著他那張可惡的臉咬了下去。
他一抬頭,我啃到了他的脖子。
「你身后有監控。」
我緩緩扭頭,和一個牛頭骨裝飾對了個眼。
那牛頭骨眼冒綠光。
還能這麼隱蔽的嗎?
我看著那雙綠油油的眼睛。
仿佛在隔空和潘華對視。
21.
謝仰運來了貨,睡了好久才緩過勁兒來。
他當著我的面兒脫衣服,身上添了新傷,胳膊上綁著紗布。
我以前以為這是他跟著潘華為非作歹時留下的傷口,可是潘華說他當過警察。
這些傷疤,會有另一個故事嗎?
「潘華說,你當過警察?」
謝仰的動作頓了頓,點點頭。
「我是警校生。」
「你哪個學校畢業的?」
謝仰揪住我的臉:「這麼好奇啊?說這些還有什麼用,反正我現在都已經不是警察了。」
也是。
我心中關于謝仰是臥底的這點猜測破滅了大半。
就算是警察又怎麼樣呢?
現在又不是。
我見過謝仰發脾氣時的模樣,聽說有人在他的酒吧里搞事,他第一次帶著大批人過去。
他給我戴上耳機,叫我玩會兒游戲。
然后他用棒球棍打斷那人的手腳。
我從屏幕的反光中看見,他臉上不曾收回的戾氣。
謝仰抱住我,親吻我的額頭。
「阿寶,今晚送我哥走,明天一早,我們就去泰國。」
「等安定下來,你想聽什麼我都跟你說。」
有一瞬間,我竟然真的覺得他的計劃可行。
ADVERTISEMENT
可是,不行。
我還有戰友。
還有父母。
還有家。
今晚,該收網了。
謝仰等不到明天一早了。
22.
是夜,寂靜無聲。
我被謝仰叫醒,他往我手里塞了一把手槍。
「拿著防身。」
我掂量著手中沉甸甸的分量,突然將槍口對準謝仰。
「你敢給我槍?」
「阿寶,你盡可以殺了我,但是你走不出去。」
謝仰笑得陰沉沉的,一點兒也不怕我開槍。
「這槍是給你防身用的,我怕我哥趁亂殺了你。」
「那你就不怕我殺了潘華?」
「只要你可以。」
「你以為他為什麼留著你?那是為了跟警察談判的時候,手上有個籌碼。」
謝仰跟神經病似的陰晴不定,可能昨天還好好的,今天就變態了。
我在心里狠狠唾罵自己,簡直在謝仰的溫柔鄉里被迷得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要不是今晚就要收網,我還真以為自己被他滿嘴胡言亂語迷惑了。
謝仰在警校絕對是優等生。
可惜,我們是敵人。
23.
被警察包圍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們都被潘華耍了。
甕中捉鱉的那只大鱉早已不知去向。
被捉的只有謝仰。
潘華放棄了謝仰,自己逃了。
冰冷的槍口對準我的太陽穴。
我再一次被謝仰挾持。
一步步后退。
看樣子謝仰想帶著我跳到河里。
河是國境線的一部分,只要逃到對岸,從此山高水遠,無人知曉。
「謝仰,水里也有我們的人,你逃不掉的。」
集結了兩地警方的追捕,這里被圍得像鐵桶一樣。
水里也有蛙人。
今天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讓潘華跑了。
幾年前潘華的盤龍集團放高利貸催債,在公交車上安裝炸彈,致使數名警察傷亡。
謝仰幫潘華頂罪入獄,最后多方操作他只蹲了一年多就出來了。
從那個時候起,仇恨就已經不共戴天。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