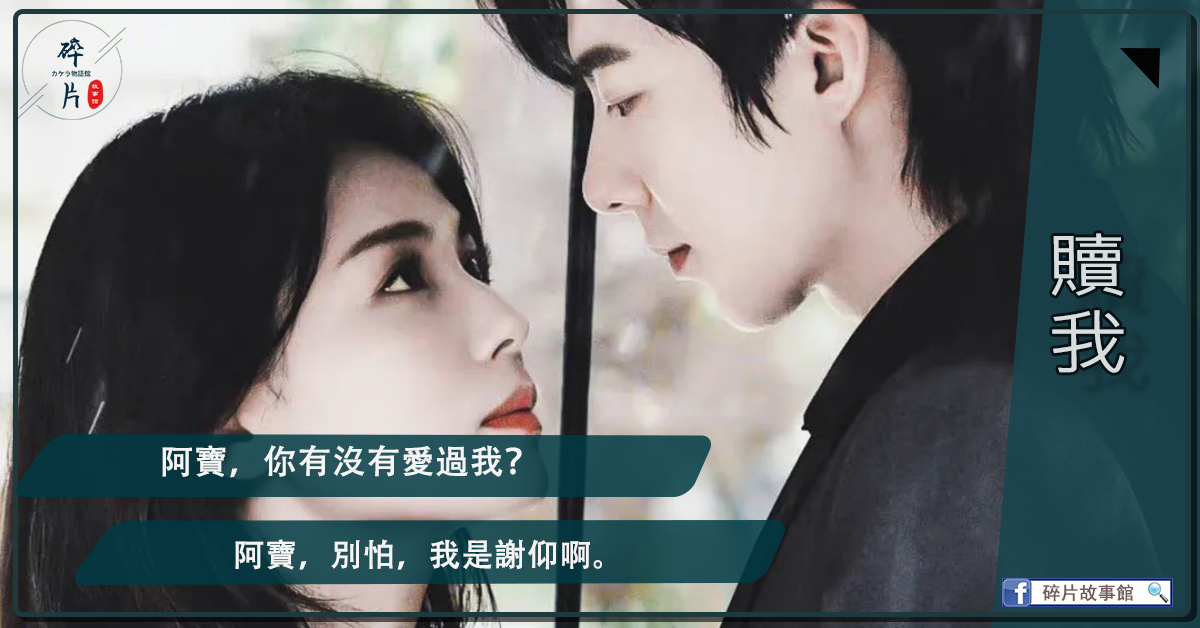《贖我》第5章
他現在在自制。
如果是土面粉,何必費那麼大勁兒從外面倒騰進來?
我聽著他們說話,腹中卻已經開始盤算,怎麼把消息傳出去。
「……你我認識,你這位謝老弟,我也聽你說過,那這位是?」
不知道怎麼,吳巴德突然注意到了我。
謝仰繃起身子:「這是我……」
「這是他妹子,從小相依為命,是個傻子。」
潘華先一步開口:「怎麼?懷疑我?」
「誒,我怎麼敢懷疑你呢,以后潘哥在緬北混出來了,我還要仰仗你呢。」
「這樣,你去接一批貨,貨接回來了,我就送你過河。」
接貨。
就是去接那些倒騰進來的貨。
風險度很高,一般都是些無關緊要的炮灰去。
有命去,有沒有命回來就不一定了。
潘華低著眼,嘴角抿成一條直線。
「吳老板,過分了吧?讓我去接貨?」
吳巴德吐出一口煙霧:「那沒辦法,咱總是要綁在一根繩上我才能放心。」
剛才還仰仗來仰仗去,現在就變得劍拔弩張。
謝仰抬頭。
「我去。」
「我替我哥去。」
吳巴德笑起來:「當然可以。」
16.
謝仰去接貨,那我們就要分開了。
「謝仰,如果你是去運毒,不管你是不是被逼的,發現了就死刑。」
謝仰無所謂道:「我現在身上都背了幾個死刑了?你有空多替我記一記,多一次我就像白得這條命。」
「我不在家,你自己小心點,誰的話都別信,誰帶你走都要跑。」
「那要是你大哥呢?」
「尤其是我大哥,就數他最想殺你,你離他遠點兒。」
我竟然無話可說。
想想也是。
潘華才應該是最恨我的那個。
從小養到大的弟弟為了一個女人把老窩都弄沒了。
而且死護著我,不許他動。
ADVERTISEMENT
我現在稍微有點理解為什麼婆媳關系處理會這麼復雜。
尤其是那種沒有老伴的。
比如潘華。
17.
這五年和謝仰綁得太緊了。
中間也沒離開過幾天。
在這種環境下,他不在我身邊,我竟然覺得缺了點什麼一樣。
臥底的意義和目的就是自己去臥底的那個人。
一個人生命中的五年都和另外一個人綁在一起,和他同吃同住,談情說愛。
然后終結他,就是我的使命。
可我只希望謝仰,栽于我手。
他的命是我的,不能假手于人。
我在住處等謝仰回來。
先等來的不是謝仰,是潘華。
我被摘下黑色頭套的時候,已經被捆在一個廠房。
本該針鋒相對互相猜忌的潘華和吳巴德,現在哪有半點矛盾的樣子?
被黑暗籠罩,又突然見到光明,我的眼睛一時無法適應,滿眼刺眼的白光。
「老大,她醒了。」
潘華坐在椅子上抽煙,他看我的樣子真的像個惡毒婆婆。
只是惡毒過頭了,惡婆婆是煩人,他是要命。
「還沒找到那批貨嗎?」
「沒呢,皮卡都快拆成螺絲釘了。」
潘華哼笑:「謝仰那臭小子,翅膀長硬了,防著我這個哥呢。」
我冷不丁開口:「你還不是防著他?」
「喲,祝警官,早就猜到了?」
18.
是的,早就猜到了。
他們是故意支開謝仰,而這邊實際的老大,也并不是吳巴德。
而是潘華。
包括這個造土面粉的工廠,多半也是潘華的生意。
而這一切,全都是瞞著謝仰的。
潘華瞇著眼,也不知道在想什麼。
「你這個腦袋瓜子,跟謝仰倒也不愧是一對,你說你要不是警察多好,我巴不得有個這麼聰明的弟妹。
ADVERTISEMENT
」
「其實如果謝仰還是警察,你們也挺配的。」
我渾身一震。
「謝仰當過警察?」
潘華有些詫異:「他沒跟你說?」
「呵,他這輩子注定跟警察攪在一起,祝玥是,你也是,你倆都姓祝,又長得一樣,你真沒個姐姐?」
我搖頭。
我是獨生女。
我也很詫異,這個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巧的事兒。
長著一模一樣的臉,又都姓祝。
難道我們是失散多年的雙胞胎姐妹?
潘華卻不給我想這些亂七八糟的機會,他抽出匕首,對準我的臉,我甚至已經感覺到了一絲刺痛。
匕首很鋒利,稍微一壓,就能劃破皮膚。
「你說,我要是劃爛你這張臉,謝仰還會不會這麼癡迷不悟?」
我直視他的眼睛,甚至臉還靠近了他的匕首。
「你劃爛我的臉有什麼用啊?」
「你不想找到那批貨嗎?」
潘華瞳孔一縮,匕首退了一退。
「你知道那批貨在哪兒?」
我大喇喇坐著,好似我現在不是在虎狼窩,而是在談判桌。
「不知道啊,但謝仰知道。你猜我這張臉爛了,他不喜歡了,你還拿什麼威脅他?」
19.
潘華臉色很難看,只是叫了兩個人看著我。
自己離開。
而我,還在消化那個讓我震驚的消息。
謝仰當過警察。
我不禁在想,有沒有可能,謝仰也是臥底?
否則,為什麼會和潘華離心?
兩個人,相互信任,相互支撐,又相互猜忌。
我睡了又醒,醒了又睡。
我都快餓死了,他們都不知道給我點兒吃的。
潘華不會把我忘了吧?
「喂,給點吃的啊!」
那個看守的人看了我一眼。
「老大不讓我們給你吃飯。」
……潘華竟然是故意的。
他果然是惡婆婆!
看守的兩個貨竟然還當著我面輪流換班吃飯。
你奶奶的。
老虎不發威你真當我不是警察?
捆住我的繩子突然松開,那兩個人嘴里的飯還沒咽下去就被我抓住后衣領,兩個腦袋瓜子一碰——暈了過去。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