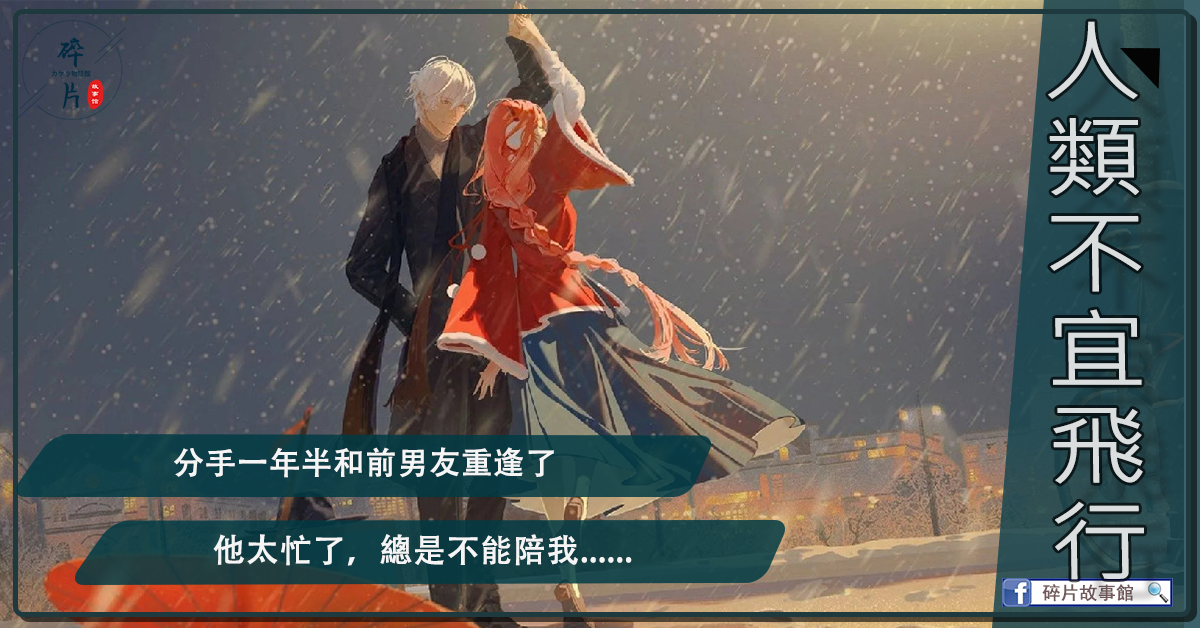《人類不宜飛行》第5章
「嗯。」鄒沉搭腔,「阿姨,司司不嬌氣。她能穿著十八厘米的高跟鞋,開叉到腰的裙子,凌晨一點搖花手……」
我一把捂住他的嘴,在他耳邊小聲而兇惡:「再多說一個字……」
我豎起小拇指,露出五百塊做的美甲:「我劃花你的法拉利,讓你開不了專車。」
「哦。」他垂了垂眉眼,又揚起嗓子,「阿姨,司司好像不喜歡我的法拉利當婚車。您看您什麼時候有空,來陪司司看看車。結婚的事情,我怎麼樣都行,主要是看您和司司喜歡。」
11婚車?結婚?
還好沒吃早飯,不然我又要吐出來。
這樣的玩笑,他以為很好笑是不是?
我和鄒沉好了多久呢?
記不清了,反正,是從學校里的兩袖清風,到他事業有成,從宿舍里壓著嗓的電話,到一起搬進這間全款的市中心大平層。
可惜我等了一年又一年,都始終沒從他嘴里等到過結婚兩個詞。
我終于累了,不等了,他現在要我有空去看婚車?
他把我當什麼?
陀螺?
玩耍著,鞭打著,擺弄著,最后還是會轉回他腳邊,一圈又一圈,樂此不疲?
這麼看,陀螺和狗的區別也實在不大。
趁著鄒沉上班之前,我先一步準備離開他家。
路過客廳時,我看見沙發上的一片凌亂,和垃圾桶里的幾枚煙頭。
我擰起沙發上的兔子玩偶,左看右看,耳朵處的縫補歪歪扭扭,還散著淡淡的煙草香。
想來昨晚,鄒沉抱著它在這里睡了一宿。
我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又抽煙?什麼時候開始的?」
「縫你兔子耳朵那次。」
他像被抓到錯處的小孩,推推眼鏡遮擋情緒:
ADVERTISEMENT
「我手笨,縫了一夜。太困了,抽幾口提神。」
「以后別抽了。」
走到門邊,鄒沉在身后叫我:「司司,幫我帶樓下扔了。」
「不扔。」
「聽話。」
我一字一頓:「我說——不——扔!」
我明白他的把戲。
他在模仿我們還在一起的時候。
我卻不明白我自己,看著他抽過的煙頭,我心在發痛。
12那之后,鄒沉沒再聯系過我。
闖入我的生活,再突然消失,他果真覺得很好玩。
不得不承認,欲擒故縱這一招,永遠老套,永遠撩撥。
過了一周,8 月 6 日,我媽打電話來說要過來陪我,我像是終于逮到個機會似的,給鄒沉發了條消息。
【我媽來了,你惹的麻煩,你解決。】
他不解決。
左等右等,我睡過去,又再醒過來。
23:39……
2:18……
3:29……
4:44……
4:59……
我從飄忽的睡夢中一次次睜眼,打開手機,空蕩蕩的消息列表,日期從 8 月 6 日到 8 月 7 日,他始終沒回復過我。
沒事習慣了,鄒沉本來就是個鬼,行蹤不定。
他肯定又是開了飛行模式,在天上晃蕩了一夜,像遠離地球的飛行探測器,茫茫宇宙中失去信號。
清晨五點多,我被電話吵醒。
錢小敏打來的,她聲音發著抖,說肚子好痛,出了很多血。
打車去醫院的路上,我盯著手機,鄒沉依舊沒有回復,我又發了一條過去。
【小敏見紅了,我好怕。】
我真心實意的好怕。
到醫院時,她已經被推進了手術室。
坐在吵吵嚷嚷的長廊上,我突然覺得很冷,也很恐懼,生命總是如此脆弱,誰也保護不了誰。
直到,我昏昏沉沉間,一個高大頎長的身影擋住了嘈雜,將一件西裝外套被披上我的肩膀。
我抬起頭。
他出現得不講道理。
ADVERTISEMENT
鄒沉,昨晚像鬼,現在像神,神出鬼沒,總是從天而降。
「遇到事了,怎麼不和我說?」
開口,他嗔怪我。
不是,他嗔怪我?他有什麼資格嗔怪我?他居然敢嗔怪他的祖宗?
我紅著眼睛昂起頭,拳頭猝不及防地重重錘上他的胸膛:「你兇誰?」
鄒沉哭笑不得,委屈不已,仿佛他已不能更溫柔一點。
「那你兇回來。」
「你為什麼不回我消息?」
「睡了。」
「和誰睡?」
「想和你。」
鄒沉蹲下來,雙目定定地看著我,仿佛在暗示我他的一手絕活:「但沒有你,就只能一個人。」
「我說,我媽來了!」
他一臉無所謂:「又不是狼來了。」
「你自己電話里惹得麻煩,你自己去解決。」
「哦?我惹得麻煩?」鄒沉眉眼垂了一下,忽得又抬起來,像是要吃定了我,「司司……」
他反客為主:
「你是在暗示我,快點求婚,好讓你媽幫忙挑婚車,讓孩子生下來叫爸爸嗎?」
我:???
他拍了拍我的小肚子:「小哪吒,你媽急了。」
你媽才……!
文明,文明懷孕,文明做人。
13不多時,錢小敏從手術室中被推出來,有驚無險,胎兒在腹中尚且無恙。
我長舒一口氣,舒得眼睛更紅了,不自覺抽泣了兩下。
我撲上去抱了下剛剛蘇醒的錢小敏,在她腦門親上一口。
「嗚嗚嗚,孩子的媽你辛苦了,母子平安真是太好了。」
錢小敏無語地擰起眉,動彈不得,只能口中默念「退退退。」
「別說奇怪的話,人家有老公了。」
鄒沉擰著我領口,把我拖走。
頓了頓,他添上一句。
「你也該有了,沈司司。」
我,有老公?
抱歉,那種好東西我沒有,我只有全天下的女人都想揸火箭發射出地球的存在——前男友!
我翻個白眼,推著錢小敏的床背過身。
「和好行嗎?」
鄒沉緊隨其后,聲音弱弱的,冷不丁一句:「我真的很想你。」
想我,怎麼想我?
我冷笑著停下腳步,打開手機,給他看我倆的消息頁面,綠油油的,比男人的頭還綠。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