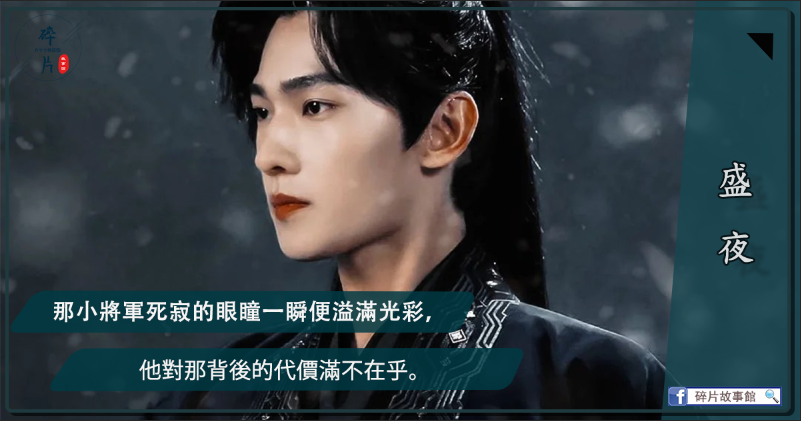《盛夜》第10章
他不言,我不語,兩人就那般平靜的生活。
直到那天兄長給我編了只小綠蚱蜢,他像小孩一樣逗我開心,這樣的兄長和夢里頭那個白發蒼蒼的老人重合在一起。
年老的他,也是這樣這樣費盡心力地逗我開心。
原來,兄長一直都是兄長。
無論夢里,還是夢外。
我把小蚱蜢放進掌心里,好奇地問:「兄長,你到底是誰呢?在你成為朝朝的兄長之前,你到底是誰呢?」
兄長捏捏我的臉,在我身旁坐下,「朝朝現在才來問?不論兄長之前是誰,都已經只能是你的兄長了。」
兄長微微一頓,接著道:「我原先只是街頭乞兒,從記事起便是。我沒有名字,不知道從何來又該向何處去。那日我同他人搶食,非但沒搶過,還被人打得頭破血流。
「我那時候以為自己會那樣死去,卻幸而被一對善良的夫婦救起。后來我成了他們的兒子,后來又成了朝朝的兄長。
「我第一次見到你時,就告訴自己,我要永遠護你左右。不只是恩情,也是因為我家朝朝那般惹人喜愛。」
我低頭,裝出一副認真把玩手里頭的小蚱蜢的模樣。
然而一顆心臟卻撲通撲通跳個不停,我想起與兄長在夢里的那一世來。他一生都未曾娶妻,一生都守候在自己幼妹身旁。
既然我們都只有彼此,那為何不更近一步?
我將頭枕在兄長的肩頭上,那些話百轉千回,終究是止于唇齒。
到底是缺乏了臨門一腳的勇氣。
那次兄長遠去云城經商,臨走時他拉著我喋喋不休地囑咐了很久。
ADVERTISEMENT
我敷衍地點點頭,說知道了知道了。
哪知兄長還未到云城,就在途中遇上了匪徒。家仆傳信說,兄長傷重,恐怕再回不了臨京。
那是此生第二次經歷這樣的惶恐和絕望。
正在我近乎崩潰時,盛燁卻問:「朝朝,你想去見見你兄長嗎?」
「畢竟……有可能是最后一面。」
我哭著說想,哪怕路途遙遠,哪怕來不及,我也想為兄長義無反顧一次。
盛燁笑得張狂,「有小爺在,永遠不會來不及!」
他拽著我的手腕,把我拉到一處偏僻的院落門口。他說:「阿朝,你家兄長就在門的那一頭等你。」
「去罷。」
我不疑有他,因為變作鬼魅后的盛燁,確實能做很多常人不可及的事。
我點頭道謝,推開那扇門走了進去。
兄長面無血色地躺在床上,他呼吸清淺,竟像是已經去了一般。
我哭著撲進兄長懷里,驚醒了彼時處于幻夢里的他。兄長虛弱地睜開眼,問我說:「朝朝?怎麼哭了?
「不對……我竟是還在夢里頭?
「朝朝,我做了一個好長的夢,夢見我以兄長的身份守了你一生。就連離世前我也在想,要是下輩子也還能守在朝朝身邊就好了……」
我用力地搖頭,埋進兄長脖頸里,說:「沈暮,不要做我兄長了,我們在一起罷……」
兄長的身軀霎時就僵硬了,他驚異地捧起我的臉問:「朝朝……你說什麼?」
我落下淚來,重復道:「兄長,我們在一起吧。」
后來我才曉得,兄長雖遇上匪徒,傷卻也只在皮肉,并不致命。且兄長也并沒有命人給家里帶信。
我沉默片刻,就知曉了其中緣由,那家仆怕是盛燁所為,是他替我作下決定,給了我最后的勇氣。
ADVERTISEMENT
出嫁那天是個明朗的好天氣,長冬已逝,三月春光和煦柔和。房檐上的麻雀在嘰嘰喳喳地喊個不停。
盛燁小小一個,站在房間的角落里巴望著我,我沖他笑笑,他也回了個明朗的笑給我。
「阿朝,你今天真好看。」
我屏退眾人走到他的身旁,他仰頭認真地凝視著我,半晌劍眉一挑,笑言道:「我有些后悔了。」
「后悔什麼?」
「后悔沒有把小阿朝娶進家門。」
我抬手揉亂他的發,「盛燁,你怎的又打趣我?」
這時屋外傳來了喜婆催促的聲音,與此同時盛燁的身體也變得透明起來。
我心中一澀,問:「盛燁,你是不是要走了?」
盛燁點頭,他上前一步,踮起腳拉住我的手腕,「阿朝快走,誤了吉時可不好!」
他說著便用盡全力把我推出門外,刺目的陽光灑在身上讓我有片刻恍然。
耳邊響起喜婆的驚呼聲,「姑娘!你的蓋頭還沒戴呢!」
我點點頭,任憑那塊紅布蓋在自己頭上。
我沒有轉身,沒有回頭,只堅定地在喜婆的攙扶下,慢慢走向另一人。
此后,便是生生死死,不復相見了。
13
那白衣孩童從陰影里走進陽光底下來,他的身軀被陽光穿透,然后一點點變淡。
他一動不動地站了很久,像是一棵樹。
這時一只白狐從墻頭躍下跳到他身旁,白狐的聲音又尖又細,它冷漠道:「盛燁,你就要消失了。你編一場幻夢,就是為了令愛人變心。」
「我很好奇,如今你可有痛、可有悔?」
盛燁不理它,只沉默地站著。
白狐也不惱,它蹲坐下來好奇地打量著他。明明已經死了很久,可他現在這表情,卻像是又死了一次一樣。
這是一個奇怪的人,它如此想。
盛燁沉默很久,才漠然地說:「你和我說過,她若與她兄長在一起,會舉案齊眉、兒孫滿堂。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