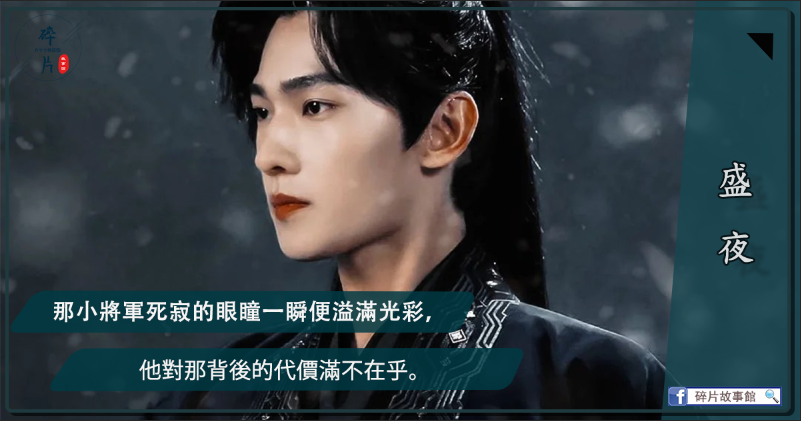《盛夜》第9章
我衣服被劃破了,非要讓你給我補……
「可是你好老好老,你眼睛花了,手也是抖的……你怎麼努力也沒能把線穿到針眼里,我一時惱了,就說我再也不要兄長了……
「你那時好失落……」
兄長緊抿著唇側,臉緊繃成一條冷硬的直線,他落下淚來,把臉埋進我的掌心。
「朝朝,兄長可以做一輩子的兄長的……」
「你都忘了好不好?」
我不答,只吃力地起身,將兄長抱進懷里。
而我那素來強大又冷靜的兄長啊,卻在我的懷里,哭得像是個孩子。
再見到盛燁時,他依然是那個不言不語的鬼魅。
縱是屋內燭火明亮,也依舊無法驅散他身上的陰影,我憶起夢里頭他騎了高頭大馬,一身喜服的模樣。
我心里一緊,卻訝異地發現,自己已經不若初時的那麼痛和絕望了。
我問盛燁:「你給我看的是什麼?」
盛燁沉默地注視著我,半晌才道:「是上一世。」
「那為什麼這一世的你死了?」
我目不轉睛地看著盛燁,想從他臉上尋得可以證明他謊言的蛛絲馬跡。
可是,沒有。
他蒼白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阿朝,我回來找你,是為了彌補自己上一世的過錯。」
我搖搖頭,「不用你彌補。」
「我心中有愧,入不了輪回。能解開的人,只有你。
11
今年臨京的冬日格外冷,才剛入冬便下了一場大雪。鵝毛般的大雪飄飄而降,很快臨京城就只剩下了最純粹的白。
我踩在軟綿綿的雪地上,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響,俯身將雪捧進手心,才一會兒,掌心就被凍得通紅一片。
一件黑色的斗篷穩穩當當地落在我身上,我大驚失色地扭頭,忙對站在一旁的小男孩說:「喂!你注意點!要是被人看去了怎麼辦?」
ADVERTISEMENT
黑色的斗篷無風自揚,然后像是有意識一樣落在一個姑娘身上,這樣的場景怎麼想怎麼詭異。
那男孩卻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模樣,他扭頭哼了一聲,「反正到時候被當作妖怪的是你,與小爺我無關!」
我食指曲起,用力地往他腦門子上一敲,「我好心收容你三年,你就是這樣報答恩人的?」
那男孩的唇高高嘟起,賭氣地扭過頭去。
看著他,當真找不出曾經騎著戰馬,一身銀甲熠熠生輝,張揚得不可一世的小將軍模樣。
我搖搖頭,忍不住抬手把他的發揉成亂糟糟的雞窩樣,近來我好像越發喜歡這個動作了。
果然,惹來了那少年的怒視。
我笑笑,問:「盛燁,你怎麼越變越小了?」
最開始,盛燁只是在白日里陽氣重的時候,才會變作小孩子的模樣,再后來,不論白天還是黑夜,他都是一副小孩子的模樣,等到現在,他又從八九歲的男孩變作五六歲的孩童。
盛燁把我的手打開,惱羞道:「那還不是怨你!」
我眨眨眼,不解地望向他。
他長嘆一聲,稚嫩的臉露出惆悵的表情,「我的執念、內疚快要散了,才會越變越小,再過不了多久,我就能飲孟婆湯,過奈何橋,重新轉世了。
「阿朝,你就快幸福了。
「就快要徹底地擺脫我這個自私、薄情、不忠的鬼魅,你……開心嗎?」
我搖了搖頭,心底升騰出一股悵然來。
「阿朝,你恨我嗎?」
寒風吹落枝頭上的積雪,新雪跌落在他的肩頭。少年眼瞳是黑夜一般的沉郁濃黑,然而他蒼白的臉龐、毫無溫度的軀體,就快要和漫天的白茫融在一處。
ADVERTISEMENT
原來,我曾經摯愛的少年和雪一樣飄忽不定。
「不恨。」
我聽見自己這樣說:「從那場大夢里醒來,我才深切地知曉生命何其短暫。朝暮交錯里我和兄長就白了發,我這一生連愛都來不及,又怎麼會去恨?」
盛燁笑了,笑出一滴滴紅色的血淚。落在雪地上,格外的觸目驚心。
他笑著說:「恨我,很好。不恨我,更好。」
盛燁身上無端地升騰起愛與恨,他落寞、悲傷、心痛,脆弱得像是風一吹就會消散。可是,我卻再也猜不透他的心事,只是覺得茫然。
我疑惑地上前,卻被盛燁狠狠地避開。
他背對著我,「阿朝,我已經困在這里太久太久了……我已經撐不下去了……」
「如今一切都快要結束了……我很開心。」
我點點頭。
曾經我以為盛燁不會變,我也不會變。后來我以為就算是盛燁變了,我依然不會變。可而今我曉得,滄海桑田,世間萬物都是活在變化里頭的。
我釋然地笑笑,「我這一生只愛過兩個人,一個是你,一個是兄長。」
「一個是少年懵懂,情竇初開帶著一見鐘情的無限歡喜,一個是朝暮相伴,經年累月積攢下的親情與愛。大抵這一生,我除了你與兄長外,不會再對第三人交付那麼多的感情。」
我將手里的雪捏成一個小圓球,輕輕呼出一口白氣又道:「我和兄長都已得償所愿,我希望你也是。」
12
曾經的我,絕想不到自己會有嫁給兄長的一天。
自那日我從漫長的夢里頭醒來后,就一直對兄長抱有復雜的感情。兄長待我一如往昔,只是那份好里頭多了一份刻意的疏離。
我知道,那是兄長害怕自己會傷到我。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