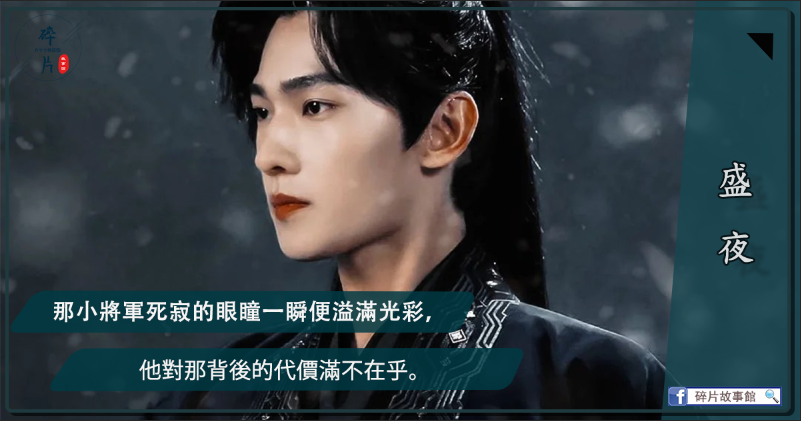《盛夜》第7章
他本該放心才是,然而久久在他胸膛里來回震蕩的,卻只有無限的嫉妒。
連他自己也說不清,究竟是從何時起,兄長不能只是兄長了。
許是相伴的每一個年歲里,她軟糯糯喚的每一聲兄長。他教會她走路識字,任憑她在自己懷里恣意撒嬌。他已經習慣了有她陪伴在側,可而今她羽翼漸豐,卻不肯再躲進他懷里了。
西北傳來戰事,盛家奉命出征。
那天他家小姑娘跟在隊尾送了很久,等到再也走不動時,她坐在地上,沒精打采地將腦袋枕在膝上。
她悶悶地問:「兄長,他會回來娶我的,是不是?」
他把柔弱纖細的小手裹進掌心里,「他會的。」
沈暮將自己奮斗半生的心血,都做了自家小妹的嫁妝,她是他捧在掌心的明珠,值得擁有世上最好的一切。
他要她風風光光地出嫁,他要她做這臨京城最好看的新娘。
西北的戰事一打便是五年,最終以盛家軍的大勝落下帷幕。
盛家軍的鐵蹄踏平了敵國的王都,敵國王上的首級被取下當作賀禮。收復失地、開疆拓土不說,更狠狠地震懾了那些潛藏在暗處虎視眈眈的外敵。
那日臨京城內萬眾齊歡,百姓們無不涌上街頭迎接他們的大英雄。
沈暮用臂彎隔開人群,小心細致地將他家朝朝護在懷里。
姑娘用盡全力踮起腳尖,在人群里頭尋找自己心上人的蹤影。然而人海茫茫,且她身材嬌小,縱是已奮力向上躍起,也只能看見一個個黑乎乎的后腦勺。
舍不得她失望,沈暮一彎腰,長臂一攬,讓她穩穩當當地坐在自己肩頭。
ADVERTISEMENT
他直起身,問:「這次可是看到了?」
那姑娘點點頭,「兄長真好!」
沈暮輕嘆一聲,「我家朝朝當真是個磨人的小丫頭片子,給你在月臨樓給你訂好的位置你不去,非要上街人擠人。」
姑娘也不看他,只道:「樓上視野雖好,但離阿盛太遠。」
「你小小一只混在人群里頭,盛家那小子便是經過了也看不見你。」
「我能看見阿盛就夠了,我已經好久好久好久沒能好好看看他了。我想把現在阿盛的模樣也好好記在心底。」
沈暮心中疼痛難當,他心里發苦,連舌尖也漫上咸澀的味道。他其實好想問問她:
朝朝,若兄長不是兄長,你可會對兄長動心分毫?
這話在他唇邊繞了千百次,卻又一次次地被他強自咽回肚子里。縱使他不是她親兄長又如何?事已至此,不過為她徒添煩惱罷了。再者,能望著她幸福,何嘗又不是一種幸福呢?
他這般想,也暗自下定決心,要做他家朝朝永遠的屏障。
這時,沈暮感覺到了肩上坐著的姑娘的陣陣顫意。他抬頭望去,這才發現朝朝面色煞白,她一張巴掌大的小臉上已經布滿了淚水。
不是歡喜的……
相反她的目光迷茫又空洞。
沈暮心里一驚,他扭頭向前看去。
人群因為那身騎紅馬的年輕將軍而沸騰起來,一陣陣歡呼聲幾欲震破云霄。
昔日的少年在經過戰場的洗禮之后,已經完全褪去青澀懵懂,真正地長成了一個可以頂天立地的兒郎。
他身披銀甲走在隊伍最前面,鮮紅的披風在陽光下好不耀眼。
只是,與他同乘一騎的,還有一個身著粉衣面若桃花的女子。
ADVERTISEMENT
盛燁一只手環在那女子腰間,目光寵溺,顯然極是著緊在意。
沈暮眸色一寸寸地冷了下來,他陰沉著臉,舌尖被自己咬出血來,濃郁的血腥味溢滿口腔。
盛家人來退親那日,被沈暮大發脾氣地趕了出去。他墨色眼眸里凝著冷然,宛若深不見底的寒潭。
那小廝被他鎮住,哆哆嗦嗦地說不出半個字來,沈暮睨著他,涼涼道:「給我帶句話給你家主子。」
「就問問他還記不記得昔日立下的誓言。」
10
這是一個極為常有的癡心女和負心漢的故事,只是這樣的故事絕不該發生在他家朝朝身上。
沈暮漫不經心地把茶杯拿在手里把玩,聽著一旁的盛燁講,他是如何如何結識新人,又是如何如何矛盾掙扎,最后又是經歷了怎樣一番差點痛失所愛的絕望,最終讓他在兩個姑娘之間做出選擇。
「呵——」沈暮諷刺地笑了聲,他的掌心明珠,何時淪落到需要讓他人挑選的地步?
他把茶杯放回桌案上,撞出一聲脆響,「盛小將軍,沈某今日請你來,不是為了同你敘舊,更不在乎你心心里歷程如何。」
「沈某只問一句,你當日之言,可還作數?」
這世上絕沒有傷了他的朝朝,還能全身而退的道理。
盛燁笑笑,「自是作數。」
說著盛燁抽出別在腰間的匕首,隨他一同前來的林侍衛嚇得瞪大了眼,驚道:「小將軍不可!」
盛燁擺擺手,俯身恭恭敬敬地對沈暮行了個禮,「沈兄,是我負了朝朝。」
他手起刀落,往自己胸口上狠狠地扎了一刀,鮮血順著冰冷的刀刃滴落而下,很快就染紅了他天青色的衣袍。
可即使如此,沈暮卻訝異地發現,他心里的恨意非但沒有減輕分毫,反倒是像地獄惡鬼一樣,吞食了他心底殘存的最后一絲理智。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