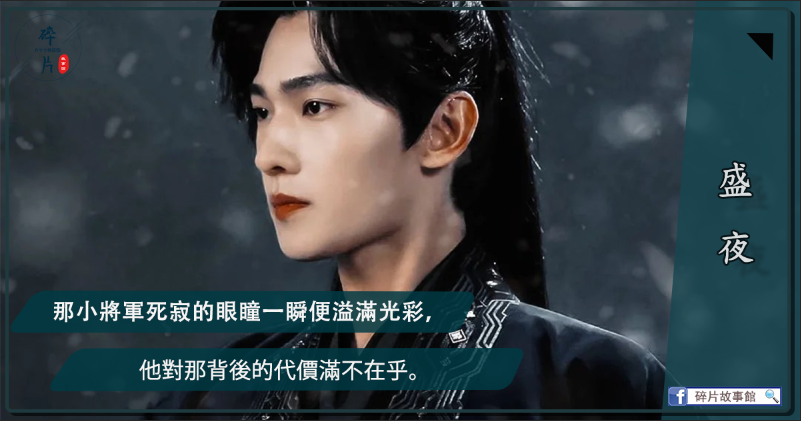《盛夜》第3章
「是林晚。」
「我書信里曾經提過的,那個曾救了我的獵戶家的女兒。」
我皺眉想了想,確實有這樣一回事。我記得盛燁那時還在信里寫:「小爺我被人家美救英雄,逼著以身相許呢。你個不識貨的小妮子,也就你嫌棄爺,若是哪天爺跟人跑了,你可沒地哭。」
我當時心里微澀,只氣惱地回了個「滾」字給他。后來盛燁寫了好一通賠罪的話給我,附帶的還有他刻的那支丑了吧唧的木簪子。
他那時說:「阿朝,爺我只同你好。這輩子爺就只追著你這小妞妞跑。」
而現在的盛燁卻告訴我說:「阿朝,我初時不覺,只道她吵人得很。哪會有她這樣的姑娘,趕也趕不走,只知道傻乎乎地掏出一顆心對人好。她在我身后站了很久,等我意識到我也心悅她時,她已經永遠離開我了。我在戰場上被人取了性命時,其實更多的是解脫。阿朝,你身邊也有這樣的人,你該回頭望望……」
我用盡全力地揮開盛燁的手,只見他半個人隱在黑暗里頭,燭火在他眉宇處投下一片陰影,襯得他眉眼愈發深邃。
他笑了,卻比哭還要難看。
5
我同盛燁一連鬧了好幾日別扭,這些日子,他像影子一樣伴在我左右,而我權當看不見他這只鬼。
大抵是知道我惱得厲害了,盛燁時常離得遠遠的,只一只鬼獨自待在陰暗的角落里。
我這時才知曉,盛燁并非只有夜里頭才能現身。他白日也能,不過這時他總是一副八九歲孩童的模樣。我猜測,許是因為白日陽氣太盛。
看著他這副小孩模樣,我總會憶起和盛燁初初相見時的情景。
ADVERTISEMENT
那時我雙親皆因為意外離開人世,尚且年少的兄長帶著懵懂無知的我前來臨京投靠叔父。
經過大將軍府時,我便見一男孩騎在墻頭上。男孩眼眶紅了一片,高高地噘起嘴昂著頭。墻頭的另一面,傳來了中年男子的怒罵聲。
「臭小子,生塊大餅也好過你!有本事你就一直待上面!」
我心生好奇,不由多打量了男孩幾眼。
不料卻被那男孩趾高氣昂地嘲諷道:「你這要飯的小叫花子滾一邊去!隔老遠都能聞到你身上的茅房味!」
彼時的我和兄長跋涉千里,確實灰頭土臉得很。聽聞有人這樣罵自己,我鼻子一酸,哇的一聲就哭了出來。
兄長向來最見不得我哭,他手忙腳亂地把我抱進懷里哄。末了還脫下自己的一只鞋子往墻頭上砸去,男孩躲閃不及,原本白凈的臉上留下了個黑色的鞋印子。
我和兄長一齊笑出了聲。
兄長見好就收,忙把我抱緊在懷里,一溜煙地跑了。
梁子便這樣結下了,后來盛燁少不得欺負我,可每次兄長都替我又欺負了回去。
而現在曾經張揚明媚的少年,正蹲在院子的角落里,委屈巴巴地盯著我看。
我有些好笑,怎的先說分開的人是他,先委屈上的也是他。
「朝朝,你在看些什麼呢?」半夏輕輕拍了拍我肩頭,疑惑地問。
「盛燁那混蛋呀!」
這話一出,我與半夏皆是一驚。
我嚇得連連擺手,焦急道:「我……我胡說八道的……」
我暗自責備自己,怎麼如此輕易就將盛燁的事脫口而出了呢?話本子里不都是那樣寫的,不容于世的鬼魂被發現后是會被超度的……
ADVERTISEMENT
等等,超度……
猛然間我憶起,那日同盛燁爭執時他說的那句:想來是我心中有愧,這才沒能轉世投胎了去。
究竟是有愧疚,還是心愿未了呢?
我怔怔地望向那個憂郁的小小少年,旁邊半夏的勸慰卻是半字也聽不進去了。
我摯愛的少年郎,他該是馳騁沙場睥睨天下的少年將軍,他該有明媚快意的一生,而不是只能囚困于陰影里,做一只見不得光的鬼魅。
「半夏姐姐,我今日有些不舒服……」
半夏止了口中的言語,她憂心地望著我,半晌又開口道:「朝朝,活著的人都該要向前看的。」
是呀,只有活著的人才能向前看。
我能,但盛燁卻再也不能了。
同半夏告別之后,我與盛燁在院中獨自對望了很久,最終盛燁先敗下陣來。他一步步從陰影底下走出來,走進陽光里,站定至我的面前。
「阿朝你這樣一直站在太陽底下,也不怕曬成炭?到時候可當真就沒人肯娶你了。」
「再有,你看看!」他舉起一只肉嘟嘟的小手,奶聲奶氣道,「你看看,小爺我身上都被曬得冒白煙了!再這樣下去,我就要被曬沒了!還有……」
我打斷他,只問了句:「盛燁,你的心愿是什麼?」
一直喋喋不休的盛燁安靜了下來,他一雙黑漆漆的眼瞳直直地望向我。
「我想你嫁人。」
「嫁給一個他愛你,你也愛他的人。」
我呼吸一窒,心里像壓了塊石頭一樣難受,「不能是你?」
「不能是我。」
6
那日過后我便同盛燁和解了,我自己思量了下,若是現在變為鬼魅的是我,而活著的人是盛燁,我可還愿意同他在一起?
大抵也是不愿的吧。
相愛易得,相守卻難。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