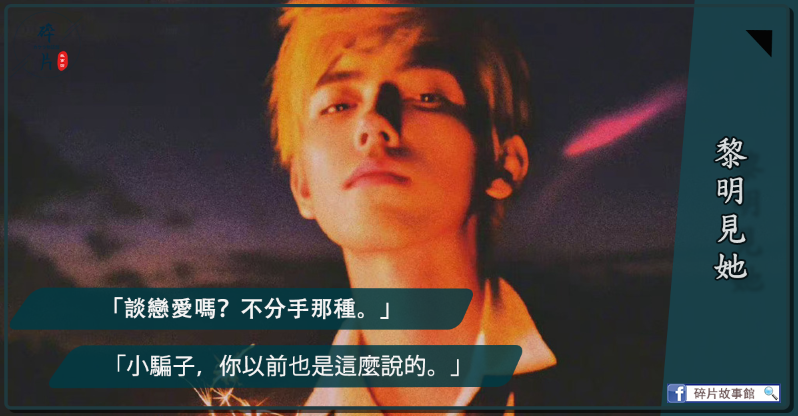《黎明見她》第11章
她纖纖細細跑動的一抹身影,揉入青灰色的天地間,像某個夜深人靜,悄悄從窗欞鉆進來的一縷月光。
很難說清楚這一刻,我是什麼樣的心思。
大抵是不那麼清白的。
后來我回憶起這個畫面,腦海里只有四個字:窈窕柔軟。
我同余窈說了,她追著我掛到我的背上,力氣軟綿綿地揪著我耳朵,罵我老色鬼。
在遇上她之前,我不信這世上有什麼一見傾心。
其實追她的那會兒,我確也猶豫過。
我很早就知道,婚姻就不是我自己的事,那是家族財產。
他們說,你的妻子一定會是哪家高門千金。
因為周圍所有人都是如此,我便也沒其他念想,反正誰也不愛,娶誰結果都一樣。
對小姑娘動了心思,我難免惶恐。
沒有把握能給她期許的未來,怕她受不了,中途撇下我就跑了。
我自詡清醒理智,偏就說服了自己。
就一小姑娘,或許也就是一段露水情緣罷了。
耗個幾年,情意消散,也就散了。
哪里想到,耗著耗著,十年了。
最不舍的,反而是我自己。
那些年,家里上下輪番說教,通常的說辭就是:和誰誰結婚,你還是可以把余窈留在身邊。
言下之意,我可以繼續養著余窈,當我的情人。
我想都沒想便拒絕了,不說余窈那姑娘不愿意,就是我,也舍不得。
她就該堂堂正正留在我的身邊,是戀人,是妻子。
20
可事情的發展,往往是進退兩難的。
他們準備對余窈動手那天,我只同他們說了一句:「要是余窈傷了死了,你們就沒有兒子了。」
那陣子的我,在他們眼中是瘋魔的。
ADVERTISEMENT
為了一個女人,值得嗎?
值不值得我算不清楚,也算不盡了。
長久的僵持后,他們做出了讓步。
我不肯結婚,那也不能和余窈結婚。
他們總盼著,或許再過個三兩年,我浪子回頭,余窈也就成過去式了。
余窈這姑娘,溫溫軟軟,乖巧可人,其實是頂聰明的,也有自己的小自尊。
她偶爾試探:「日后你要是不愛我了,可要和我明說,別對我做殘忍的事。」
所謂殘忍的事,就是怕我一聲不吭離開。
回到原來的人生軌跡,與誰結婚生子。
她頗為認真地說:「你不愛我我自己會走,斷不會糾纏。」
我哪兒舍得走啊。
那麼長的十年,她以千萬種姿態,無聲無息地,融入我的骨血。
我們完整得如同一個人。
這世上再難找到一個如她這般的人,滿目滿心,清澈簡單地,只有我。
我細細想,或許是我更怕失去她的。
所以明知道不能給她婚姻,依然自私地把人綁在身邊。
姑娘自是也明白的,從不愿讓我為難,唯一一次提起結婚的問題,鬧了個小情緒。
半道又心疼我,急急拐了個彎說不愿意嫁給我這個糟老頭。
我什麼都明白,心痛在所難免。
只能日后越發嬌寵,事事細致周全,不允她受半點委屈。
所有人都沒想到,最先跑的,是她。
很長時間,我是預感過離別的,以她的性子,或許是會在某個無人的午后,提上行李輕輕關上門,無聲離開。
我從不懷疑我的余窈,她愛我勝于她。
她會屈服于自己的愛,成全我的人生。
年少時看酸書,常有人說:所愛隔山海,山海皆可平。
ADVERTISEMENT
我嗤之以鼻。
有了她,我忽然就笑年少的自己淺薄。
有些愛,或不能平山海,卻也沉重如山。
車禍發生后,警察通知我去認領遺體。
那天所有人都以為我會瘋,我卻出乎意料地平靜。
認了人,等在殯儀館外,送她的骨灰盒進墓園,為她豎碑。
整個過程,我都是安靜的。
有人來安慰我,我笑著說:「走了就走了吧,小沒良心的。」
連一聲招呼都不打就跑路,還騙我說只是去做個頭發。
身邊的人都松了一口氣,應當是覺得我對她已經沒了什麼情意,如今擺脫,也算松了一口氣。
他們就是這麼沒血沒肉的。
除了參與「綠洲未來計劃」項目的人,沒人知道我偷偷把余窈藏進了另一個世界。
可令我崩潰的是,系統出了 bug,她留在十九歲的那天循環,而我也不能和她連接成功。
三年聽起來著實不算短,我日日耗在項目里。
自余窈離開,我從未同人提起過她。
旁人皆以為我是看好這個項目的前景,故而為此廢寢忘食。
無人知曉的三年日夜,我獨自坐在空蕩蕩的房間,想起她臨走前打來的那通我沒接起的電話。
然后一遍遍聽著她最后給我的留言。
指間的煙燒了一根又一根,煙霧繚繞,我想,那時候我的眼睛常掉下眼淚,是被熏的吧。
我并沒有因為她哭,心臟麻木沒有痛感。
每每聽了她的聲音,也只會輕聲回應她:「余窈,我也想你了。」
21
夜深人靜,無人回應我的聲聲呢喃。
我后知后覺,原來我的余窈,真的不在了。
有一次忍不下去了,深夜驅車去了她的墓園,如同一條被遺棄的狗,失聲痛哭。
那一刻,我變成了年少鄙夷的那類人。
花費三年攻堅一道難題,我成功連接上她的世界。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