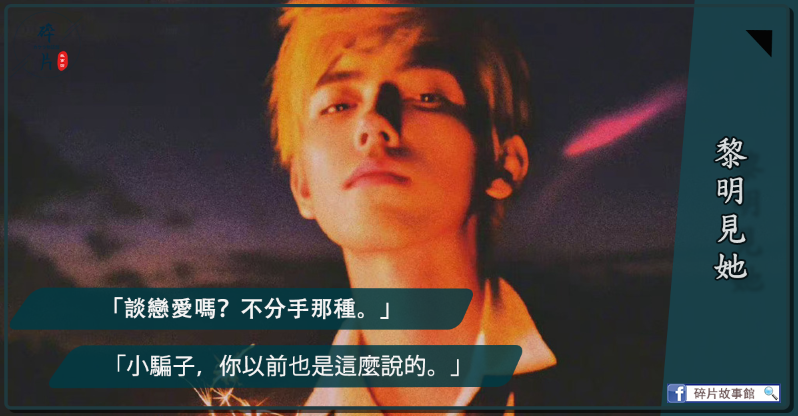《黎明見她》第8章
只要黎倦舟不結婚,我就是他的唯一。
能不能要一個妻子的身份,不重要。
只需要,他永遠屬于我,我也永遠只屬于他。
我從不和黎倦舟提結婚的事,他也不提。
黎倦舟的情話,永遠說得婉轉。
情到濃處時,他也會抱著我一遍遍說愛。
每每這時,我就生出一股子矯情勁,摟著他的脖子追問:「那麼多漂亮的姑娘往你身上撲,我又不好看,你愛我什麼?」
看吧,我是那麼俗氣的一姑娘。
明明他已經是個極致完美的愛人,我卻仍拼命想要找他愛我的蛛絲馬跡。
他慣常不正經,也沒如我愿。
惡劣地掐著我腰上軟肉:「身嬌體軟,易掰折。」
這之后自是無休止的纏綿。
成年人的愛情,是不動聲色的熱烈。
黎倦舟完美演繹了這一點,他的深情,只有我知道。
我常為之慶幸,旁人投來的目光,卻居多是不友善的。
跟在他身邊那麼多年,我總避免不了在某次宴會、某次朋友碰面,聽到一些不友善的話語。
他們私底下稱我為黎倦舟豢養的金絲雀。
什麼戀人,不過是一個笑話。
徐洋也是這麼覺得的。
他為黎倦舟工作,我見過他幾回。
有天他喝醉了,趁著黎倦舟起身去打電話,問我:「你要一輩子當黎倦舟的情人嗎?」
15
我聞言皺了眉頭,心中一陣不適。
「情人」這兩個字,太刺耳了。
我忍著不適感,冷淡回他:「我和他是正常戀愛,不是包養。」
徐洋聽了我的話,像是聽到了笑話,用十分可笑的眼神看著我。
「你跟他十年,他要是真的愛你,會不娶你?」
是吧,不只是徐洋,很多人都這麼覺得。
ADVERTISEMENT
只是徐洋直白地說了出來。
在普羅大眾的眼中,一個有責任擔當的男人,是不會讓一個女人沒名沒分跟他十年的。
我并不想反駁他,他說的也沒錯。
「黎倦舟不也沒結婚嗎?」我是這麼回答他的。
所有人都說黎倦舟注定是逃不開聯姻的命運的,但他不是堅持下來了嗎?
徐洋罵我:「窈窈,你這是自欺欺人。」
「你就沒想過嗎?是,黎倦舟現在是還沒結婚,但他也沒娶你不是嗎?」
「他給自己留了后路,隨時可以全身而退,那你呢?」
饒是他這麼苦口婆心,我仍然無一絲動搖。
我如此篤定,黎倦舟是只屬于我的。
除了婚姻,他有什麼,都慷慨給了我。
當然了,我也可以再貪心一點,去和他提出結婚的請求。
但我知道,這會讓他為難。
他的人生,不只有我啊。
徐洋恨鐵不成鋼:「二十八九了,你怎的還和以前一樣天真?」
談話終止于黎倦舟推開包廂的門。
這天回家的路上,我忘了是因為什麼了,反正是挺小的一件事,我卻突然和他鬧了脾氣。
徐洋說我自欺欺人,是對的吧。
黎倦舟一貫有耐心,哄人時寵溺的調調:「小祖宗,我呼吸影響到你的心情了?」
我一秒被他逗笑,氣呼呼地捶他的胸口。
鬧完了,我們在車內安靜了下來。
我還是沒忍住內心的躁動,小聲問:「黎倦舟,你想結婚嗎?」
能感覺到,我拋出這個問題的時候,黎倦舟的身體緊繃了一下。
很快恢復如常,托起我的下巴看我的眼睛:「你想嗎?」
車內沒開燈,窗外月明,我便也能看清他的表情。
依舊是往常柔情繾綣的模樣,只是眼睛里,浮動著一絲不自知的晦澀。
ADVERTISEMENT
我的心頓時開始細細綿綿地疼了。
我是那麼堅信的,如果這一刻我點頭,黎倦舟會遂我的愿。
但是,這也意味著,他會失去很多很多。
狹窄的車內空間,短短的一兩分鐘,我腦海中已經掠過無數個畫面。
他生來就在云端,若我非要把他拉入泥濘,他會如何?
在這個充斥著勢利的圈子,他娶了個沒有家世沒有能力的女人,縱然日子美滿,可他再也夠不著高處。
那些以前在他這里低過頭的人,會時不時踩他一腳。
更壞的是,生意場跌宕起伏,他若遇上了難關,我拿什麼幫他?
最終的結果,是他落魄歸入平庸。
和所有普通的中年人一樣,為了生計奔波,看人眼色。
我愛的那個黎倦舟,不該是這樣的人啊。
他就該在云端,驕傲耀眼。
愛到極致,連讓他為難都舍不得。
我逼著自己清醒,笑得嬌嗔做作:「我才不想,誰要和你這個糟老頭子結婚。」
16
那一年,我二十八,黎倦舟三十六了。
二十八歲的女人,不說老,但也足夠成熟,是當婚的年齡。
我猜,黎倦舟也是能看出我故作嬌嗔后的心思的,他沒點破。
我們默契地保持著一故的平和,在每個日夜相依。
要說我和黎倦舟的分開,也是很平淡的。
不過是某日尋常的午后,他一要好的兄弟來家里吃飯。
中途黎倦舟離席,去書房處理一個緊急的工作。
飯桌上,只有我和客人。
男人慢條斯理地喝了一口紅酒,開腔:「倦哥第一次把你帶在身邊,我見你的第一眼,心想這姑娘也就比其他姑娘干凈溫順點。
」
我微微詫異抬頭,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開了這個話題。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