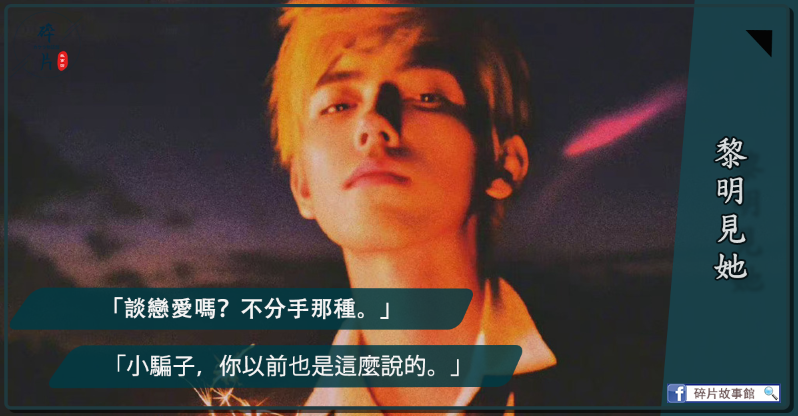《黎明見她》第7章
」
我并不為此驚訝。
黎倦舟這麼看重的項目,有我這個試驗者,他們遲早可以攻破技術壁壘。
這時我算明白了,黎倦舟為什麼可以那麼篤定循環不會結束。
因為他是主導者,他不點頭,沒人敢上線新的研究成果。
他這次走,就是為這件事吧。
我終于不得不承認:「原來你說的是真的,黎倦舟真的不會回來了。」
黎明將曉,陰沉的天竟然開始淅淅瀝瀝飄起了細雨。
涼絲絲的雨水撲在臉上,我心頭悲涼難抑。
我問:「開始了嗎?」
之前那麼多次的循環,這個時間都是不下雨的。
系統修補更新開始,循環結束了。
黎倦舟不再屬于我。
13
這個認知,讓我心如刀割。
力氣一點點被抽干,我幾乎站不穩。
徐洋伸手來扶,我躲開了,譏笑道:「你也是來檢驗試驗成果的?」
徐洋靜靜注視著我,眼神里,多是憐憫。
我了然:「哦,你是在可憐我。」
難得他還念著過去的情分,見我被黎倦舟騙慘了,所以大發慈悲來告知我真相。
徐洋側頭看向長長的胡同另一端:「我是心疼你。」
我記得和他的過去,心想著他這點心疼,應該和愛無關。
不過是對同自己一起長大的玩伴的憐憫。
「謝謝,再見。」我拖著沉重的步伐回到家,沉沉陷在沙發里。
目光無意識地看向臥室門口,想起那天來。
黎倦舟就倚著門框,他同我說:「嗯,我現在是你的了。」
我捂著心口,痛得無法呼吸。
腦袋毫無征兆地一陣尖銳刺痛,昏厥過去之前,我知道時間已經開始瘋狂加速。
再醒來時,我坐在黎倦舟曾帶我來過的花房那架鋼琴前。
ADVERTISEMENT
指尖跳動,我竟不似當日那麼笨拙,彈出的音律悠揚完整。
我從锃亮的琴蓋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面容素凈,眉目是江南姑娘的溫婉柔和,不是什麼驚為天人的美女,勝在五官端秀,氣質恬淡。
徐洋沒有騙我,我早就不是十九歲的姑娘。
現在,我回到了我的二十九歲。
我忽然悲從中生,撲在琴身上哭出聲。
和黎倦舟的故事,橫跨十年,說來很長,又平淡如水。
我們的相遇,確也是在我被徐洋甩掉的那天黎明。
自那天起,他如同一陣春風,吹進我波瀾不驚的生活,驚起一池的漣漪。
眉目清貴的公子哥,頻繁光臨平庸少女的人生。
一開始我是抗拒的,但那人啊,是從容有度的戀愛捕手。
我使出渾身解數的青澀抵抗,于他不過是一場擒獲拿捏的情調。
故事的細節極致動人。
十九歲生日,他來找我。
二十七歲的男人,矜貴動人,脫下奢牌西裝鋪在天臺的地上讓我坐下。
他端著一個小蛋糕,巴掌大,和他的身份極不相符。
我開玩笑說他吝嗇。
其實黎倦舟是個大方的人,但他知道我想要的是什麼。
名牌禮物,賓客滿堂的豪華生日宴,并不能使我歡心,反而忐忑不自在。
他太會了,讓我的眼里只剩下他。
那晚,黎倦舟用打火機點燃蛋糕上細細的蠟燭,笑道:「剛剛好。」
一個小蛋糕,我們倆剛好能吃完,只有我們倆,和旁人無關。
后來我常想,黎倦舟早就知道我們在一起會是什麼樣的局面。
那場戀愛,不會有人祝賀,只有我們兩個。
ADVERTISEMENT
他瞇著眼,在燭光搖曳里和我對視:「來,許個愿。」
那雙眼睛像一個漩渦,我一點點陷進去。
忐忑問他:「黎先生,你圖什麼?」
我甚至想,他是不是也像那些個有錢的男人一樣,有錢閑情多,包養個女大學生玩玩兒。
當然了,這是最現實,也是最可能的解釋。
畢竟我如此地平庸,有的,也不過是一副年輕干凈的軀體。
黎倦舟眸光專注:「你是一張讓人喜歡的白紙。」
「然后呢?」
「我想嘗試看看,把這張白紙都寫上我的痕跡。」
明明話意應是有些曖昧的,他坦坦蕩蕩,讓人很難懷疑他有其他暗示。
這晚到最后,他說:「我想要一個完全只屬于我的愛人。」
14
這是故事的開始,于我,像是一場夢。
這個夢,我做了十年。
故事其實也不是很難講,無疑是,我在年少青艾之時,遇上了一個身份不對等的男人。
他溫柔地牽著我的手,帶我走進了他的世界,一去十年。
那些年,他待我極好,給足了安全感。
我們如所有熱戀中的情侶般,做盡一切相愛之事。
黎倦舟是個富有情調的男人,他的愛,溫柔浪漫,纏綿悱惻,引我著迷沉淪。
真如他所說,我這張白紙上,涂滿的都是和他相關的痕跡。
我被他的愛意包圍,熱烈欣喜,又難免忐忑難安。
自踏入他的世界那一天開始,我便聽宴席上一姑娘酸溜溜地說:「黎倦舟遲早是要聯姻的,外面的姑娘,無非就是一時興起。」
他們那個圈子,愛情是至高無上的奢侈品。
唯有盤根錯節的利益,是最牢固的。
我并不愚笨,自是明白的。
但黎倦舟總能輕易就把我的不安消弭,他吻過來,說著情話。
他說:「余窈,你是獨一無二的。」
人啊,就是這麼矛盾,一邊清醒一邊沉淪。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