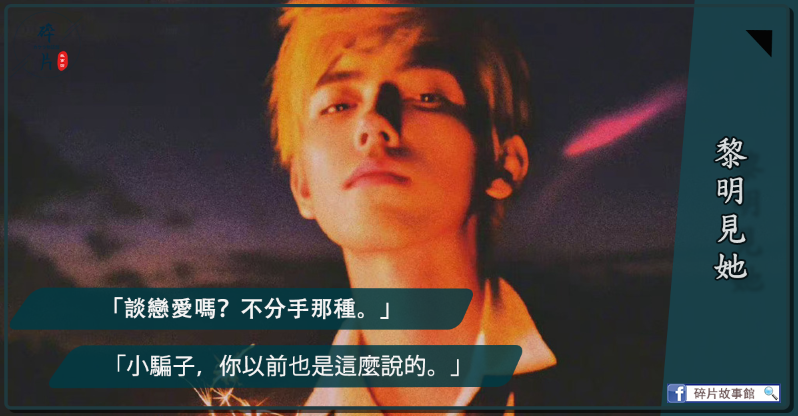《黎明見她》第3章
房間里沒開燈,薄沉的天光落入窗欞。
他坐在床畔,目光虛虛落在墻上的掛歷上。
似側著臉眸色深深望我,叮囑道:「記得打蝴蝶結。」
5
看著沉沉睡去的男人,我是懵逼的。
我幾乎可以肯定,這貨明知道我要干什麼,還主動送上門來,陪我玩這出幼稚的游戲。
「奇怪的男人。」我嘟囔著,沒忍住男色的誘惑,在他清雋的臉上摸了一把。
房間里找不到趁手的東西,我索性取下他的領帶。
然后象征性地綁住他的雙手。
其實綁不綁意義不大,我很篤定,他不會跑。
他想玩兒,還挺享受。
傍晚時我爸媽進門,他還沒醒,我關好臥室的門,坐到餐桌前。
安靜地聽著他們絮絮叨叨。
「窈窈,爸爸媽媽要離婚了。」
「以后爸爸媽媽不會再和你一起生活,我們早該有自己的人生了,為了你,一直死撐到現在。」
「你今年十九,是個大姑娘了,要學會照顧自己。」
「窈窈,以后的路,就要你自己走了。」
我內心再無波瀾,平靜點頭:「嗯,你們走吧。」
他們帶著各自的行李離開,我送他們到門口,看著他們消失在灰蒙蒙的胡同盡頭。
輕輕說了聲:「祝你們幸福。」
家里一下子就空了,只剩下我一個人坐在沙發上長久發呆。
其實我早就知道,我于他們,是個累贅。
自打我懂事開始,我媽總是歇斯底里罵我:「都是因為你,沒有你的話,我不會這麼不幸。」
我爸不常回家,偶爾回來,總會說:「窈窈,若不是你太小,爸爸連這個家的門都不愿意踏進一步。」
然后,他們便又開始漫長的吵鬧打架。
ADVERTISEMENT
我十九歲的人生,是被嫌棄的小半生。
至今我仍想不明白一個問題:明明不是我決定要不要出生,那麼,到底是誰希望我來到這個世界的?
想不明白,心在黑暗里一遍遍被揉碎,又一次次自愈。
怔愣間,感知到男人沉沉的視線落在身上。
我整理好情緒,笑嘻嘻轉頭。
四目相碰,我恍惚在他深邃的眼里,看到了難掩的痛色。
像悲憫,像心疼,千般糅雜難辨。
我不明所以,想探究,卻在看到他的樣子時樂了。
成熟矜貴的男人倚在門框邊,領帶把雙手綁在一起,上面打了一個漂亮的蝴蝶結,突兀又滑稽。
我惡趣味地揚唇:「我沒有忘記打蝴蝶結哦。」
他緩緩靠近,咫尺之間,他的手背輕輕摩挲著我的臉頰。
「嗯,我現在是你的了。」
6
周圍暗沉,他低沉的聲音敲落心間。
我心潮洶涌,怔怔看他,如被勾了魂魄。
這種感覺很奇妙,在這一瞬之間,恍惚這一幕似曾相識。
「你……到底是誰?」
我記憶里,關于這個男人,空白一片。
可他出現在我的世界里,嫻熟自如,如來過千千萬萬遍。
如謎,如霧。
他附身湊近我的耳畔,氣息繾綣:「小沒良心的,連名字都不記得了。」
酥麻感自耳際傳遍全身,我怔怔看著他的眼睛,腦子空白。
這人垂眸專注看人時,眸底盛滿深情,恍似下一刻便能溫柔地吻上你的唇。
我往后縮了縮:「你認錯人了。」
眼下這情形,我只能想到這個解釋。
空氣寂靜幾秒,他慢慢直起身。
自嘲地輕笑道:「是啊,太想她了,看誰都是她。」
我莫名有些失落。
有這樣的心情無可厚非,誰被這樣的男人看著,都得臉紅心動。
ADVERTISEMENT
又可惜,他眼中的人,不是我。
我掩飾地嗔笑:「不是說你是我的了嗎?還想著別人呢?」
也不知道我的話點到了他哪根神經,惹得他突然失笑。
「笑什麼?」
他答非所問:「黎倦舟,記住了?」
黎倦舟,黎倦舟。
三個字悄然無聲從我唇齒間滑過,竟似曾念過無數遍。
我撐著下巴好奇問:「你不是說你很忙嗎?為什麼還愿意陪我玩這種無聊的游戲?」
綁他,我是突發奇想。
可他這樣一眼就能看穿人心的男人,還上趕著陪我瘋,倒真耐人尋味。
他用牙齒咬開蝴蝶結:「大抵是無聊吧。」
「也對。」我深以為然。
被困在虛無乏味的同一天,最初的新鮮勁褪去,細想下來,其實一切都無甚意義。
遇上我這麼一個同遭遇的姑娘,順水推舟玩玩也能排解無聊。
見我認真了,他又笑了笑。
坐到我身邊,逗人般笑道:「再說,嫩芽似的小姑娘,我終歸是占了便宜。」
說來也很奇怪,我并不怕他真對我做什麼。
可能是因為擁有無限循環的時間,也就無所畏懼了。
最壞的結果,他若真有壞心思,我抵死不從一頭撞死。
明天我照樣能活過來。
「那你明天可要裝得像一點。」
「裝?」他撥弄著打火機,「我更喜歡來真的。」
來真的?
我愣了愣,他在此時彎腰,目光里瀲滟著溫繾的深情。
「余窈,我們談一天戀愛吧。」
「余窈」兩個字自他唇中逸出,親昵繾綣,萬分柔情。
我如著了魔:「好啊。」
7
說來匪夷所思,困在同一天的第三年春天,我遇上了一個叫黎倦舟的男人。
他就像是在那個清晨,在霧里化出了形,飄然而至。
而我,為之著迷。
黎倦舟無疑是個完美情人,沉穩寬容,溫柔深情。
循環的每個清晨,我一醒來站在胡同口,他會第一時間牽起我的手。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