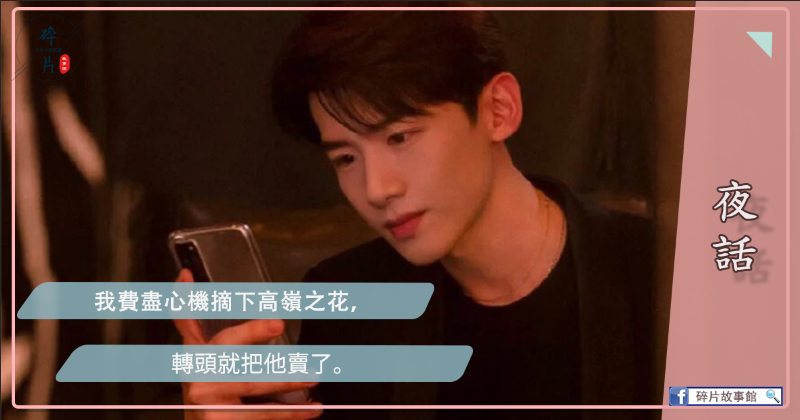《夜話》第12章
「走吧。」他收回手,脫下身上的風衣披到我身上,握著我的手腕便把我帶到了傘下。
手腕處他掌心的涼意侵入皮膚,我被他帶著下山。
懵懂側頭問他:「去哪?」
「民政局。」
19
我聞言腳步一僵,不動了。
有點好笑地問:「酒還沒醒?」
要是昨晚他說這樣的話,我大概會認為他是借酒裝瘋。
「我很清醒,比任何時候都清醒。」
「那為什麼說胡話呢?」
我只當是一個玩笑,沒做他想,繼續往下走。
手腕一緊,他稍用力,把我帶到身前。
親密無間的距離,他微彎身,氣息略惡劣地撩過我耳窩:「怎麼,不敢?」
挑釁的語氣十足,玩激將法呢?
我苦澀地勾了下唇角,想說點什麼,一時不知該如何說起。
程息梧保持著彎身的動作,目光深深罩著人,等著我開口。
四目相對,無聲對峙,我妥協地聳了聳肩:「不是不敢,是沒有意義。」
婚姻于我,實在沒多少現實意義,我既不需要它給我帶來權益的保證,亦不需要那張紙約束對方。
要走,要留,隨心就好,強求沒用。
「有意義。」程息梧眉目冷肅,字字認真,「你是程太太,就是全部的意義。」
我瞧他這認真勁,就想逗他:「當初分手你媽給了兩百五十萬呢,要是以后離婚,我要的可就不是這個數了。」
程息梧瞪我,沒好氣地說:「你對浪漫過敏?」
這樣的氣氛下,我確實有那麼點煞風景的意思。
「我對你過敏。」歸根結底,我就是羞于面對他這樣。
還是冷著點吧,現在怪讓人難為情。
程息梧的眼風冷颼颼刮過來,也沒耐心和我瞎扯,抓著我的手往山下走。
ADVERTISEMENT
「要能離婚,我凈身出戶。」風大雨急,他走得快,半條褲子都已經濕了。
看樣子,他是來真的。
「程息梧。」我嘆了聲,「你真的瘋了。」
我孤身一人,便是真的和他領了這結婚證,也無人無事煩擾。
而他有家人,他總要有個交代。
這樣不管不顧,實在不是他的作風。
程息梧轉過頭,眸光有火灼灼:「那你就陪我瘋一回。
「既然你覺得和誰結婚都沒什麼意義,為什麼不能是我?」
邏輯滿分。
是啊,和誰在一起都是未來難測,那還不如選最初的那個人。
總歸是能少些遺憾。
我許是腦子發熱了,笑著點頭:「行啊,以后你別喊后悔就行。」
程息梧哼聲,走得飛快,生怕我現在就后悔一般。
我們像兩個瘋子,在大雨連城的早上,帶著一身的水汽沖進民政局。
出來時,兩個人又矜持地收起那股瘋勁,身份轉變的生疏感充斥在我們之間。
車內稍顯狹窄的空間,我們一時無言,空氣凝滯般的安靜。
我想著總該說點什麼,轉頭看向駕駛座。
程息梧也正好側頭看過來,四目相對,他先啟唇:「你好,程太太。」
我瞬間莞爾:「恭喜啊,程先生。」
20
回家的路上,我想到了些舊事。
大學時和程息梧談戀愛那會兒,我勇敢而無畏,挖空心思想要占他便宜。
每一次都能被他嚴詞拒絕。
他比誰都矜持,連牽個手都要醞釀半天。
想到這,我生出壞心思,故意惆悵地說:「我有點后悔了呢。」
「以前我那麼撩你,你就跟神仙入定般,你……是不是不行?」
「嘶——」
尖銳的剎車聲,車子恰好停在紅綠燈前。
程息梧黑著臉瞪我。
ADVERTISEMENT
我不怕地打趣道:「早知道該驗貨再拿證,虧了。」
「你再不閉嘴試試看。」程息梧咬牙切齒,警告的意味明顯。
我識相地閉嘴,卻瞥見他耳根子紅得滴血。
這人還和以前一樣,臉皮薄得要命。
要把故事從頭說起,當初我追程息梧,除卻他人長得好、品行端方外,還因為他挺好玩。
我那時混,慣會不著四六地撩人,每一回他眼神挺嫌棄,耳根子卻紅得不像話。
所以我就越發喜歡不正經地逗他,就我那不靠譜的德行,也難怪他會認為我只是走腎不走心。
程息梧能經年累月等在原地,他比我堅定執著。
思及此,內心難免波涌。
「程息梧,我以前是有點輕佻。」
「嗯。」
「以后我會正經點。」
「嗯。」
我看了他一眼,挺認真地說:「但我現在是持證上崗,說什麼都不算輕佻對吧?」
程息梧這下子憋不住了,無奈地勾唇笑了。
氣氛總算是輕松了些,我精神松懈下來,倚著座椅開始犯困。
模模糊糊之中能感覺車子停下了,被人抱在懷里上樓。
我也懶得犯那矯情勁,大大方方地在他懷里找了個舒服的姿勢,拉著他陪我睡。
昨晚沒睡好,確實是困了。
人一沾床,就睡過去了。
醒來時,程息梧已經不在身邊。
我揉著眼睛爬起來找人,忽被客廳里的人嚇得愣在原地。
程息梧的父母不知道什麼時候來的,正壓低了聲音和程息梧說話,一旁,顧明瑤撐著下巴百無聊賴地坐在吧臺邊。
「小枝,起來了。」程息梧背對著我,最先看到我的,是他母親。
她笑吟吟迎上來:「嚇到你了?」
我緩過神來,挨個叫了人。
著實是有點不好意思:「您怎麼來了?該是我拜訪你們才對。」
「和我客氣什麼。」她無所謂地擺擺手,「本來是想讓息梧帶你回家吃頓飯,又怕你拘束,索性我們就來了。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