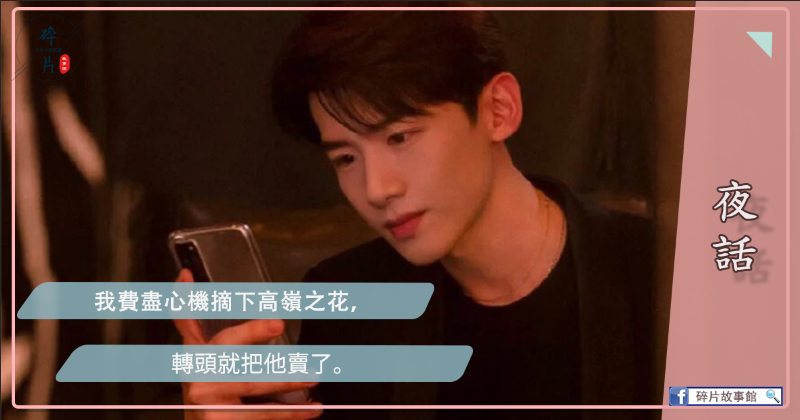《夜話》第11章
我錯愕了一下,心尖難忍抽痛。
看來我在他那,確實是個不靠譜的人,就沒給人什麼安全感吧。
覺著好笑,我嘴貧了一句:「或許,我本來就不該回來呢。」
程息梧抬頭,惡狠狠瞪過來,頗有警告的意味。
「好,我錯了。」我端正態度,認真說,「決定不要你,其實也就一件很小的事。」
「小事?」程息梧緊皺起眉頭,隱約有發火的沖動。
「對啊,極小的事。」我風輕云淡地說起,「我父親自殺那天,送到你們醫院搶救了,我當時六神無主,只想到你,跑去你辦公室找人。」
「你和同事在聊天,人家問你,那個天天來找你的小姑娘是誰,你怎麼回來的?」
我深吸了口煙,濃烈的煙霧入了肺腑,教人清醒。
程息梧的臉色微變了變,沒接腔。
「你說,就一挺煩人的小孩。」我吐出一個漂亮的煙圈,微笑著看它在空氣里消散。
再度提起這事,當時情景,歷歷在目,又像已經很久遠。
那些崩潰的,難過得要死的心情,已然消失,無了蹤影。
我并不怪他,心思也淡了。
「我……」程息梧似要解釋,最終欲言又止。
我并不需要他任何解釋,還有心情打趣道:「看吧,其實我也沒那麼戀愛腦。」
「我這人,可以奮不顧身、飛蛾撲火般去追你,但在感知到恥辱時,一定會停止。」
如果我滿腔愛意贈予他,他卻只感覺到了煩擾和嫌棄,那麼,我便不是勇敢,而是作踐。
所以做出放棄程息梧的決定,我僅用了那麼一個瞬間。
一支煙抽完,談話也即將結束。
把往事攤開,我反而輕松了許多。
到底是歲月把人的棱角都磨平了,再也沒有那股子熱情和精力和他作,和他鬧。
ADVERTISEMENT
我釋然笑開:「不可否認,現在見你依舊心動,但確實已經沒了當初那股非你不可的勁了。
「有你是錦上添花,無你也能安靜平和,得失不想計較了。」
夜深了,越來越多的燈光熄滅,程息梧的眼睛里,鋪開墨一般的暗,有深晦的痛意。
我想,他也早就看出來了。
多年再見后,我再看他,已經沒了最初的熱烈,愛意無波無瀾。
他該是有些難過了,卻仍然一直糾纏難斷。
還是會心疼。
我含笑問他:「程息梧,這樣的我,你還想要嗎?」
18
這晚長街袒露心扉的談話,以他的沉默收尾。
他沒回答。
送我回家后,也沒在我這過夜,走了。
我便默認是他已經做出了回答,解開了心結,不會再繼續糾纏,各別兩寬。
晚上睡得不安穩,我還是早早爬了起來,去了一趟山里的寺廟。
照常給我父親上了香,去見妙塵師傅。
她依舊把茶斟滿杯,白煙裊裊浮沉,我盯著出神。
「有心事?」
我坐端,輕搖頭。
妙塵師傅了然一笑:「和那孩子做了了斷?」
「真是什麼都瞞不過您。」
「難過嗎?」
我偏頭看向窗外,院里的綠樹迎風舒展枝丫,春意盎然,一切都好。
釋然彎了彎唇:「難過不可避免,但人和人之間的緣分,隨緣就好。」
以前總過于強求,想抓住父母親緣,渴望戀人長情。
到頭來才明白,人和人之間,所謂情緣,不過是一站來一站往的旅人,來來去去,都是常態。
我能做的,無非就是,他來時歡喜,他要走,笑著揮手告別。
人生啊,本該如此。
「你算是悟明白了。」妙塵師父細細瞧了瞧我,「這些年你脫胎換骨,真像變了一個人。
ADVERTISEMENT
」
接著又嘆氣:「你父親的事,對你打擊很大,他要是知道你現在的轉變,不知道該高興還是難過。」
人生不過如此,最后所求,不過內心安寧。
可我悟來的安寧,是建立在全面崩塌的人生之上,是不幸,也是幸吧。
我伸手拿起燙手的茶盞,偏著頭柔聲:「他以前總嫌棄我鬧騰,現在剛好。」
妙塵師父凝頓片刻,隱晦提了一句:「你母親這幾年也常來,多次向我打聽你的近況。」
在她要勸導之前,我決然開口:「我和她,沒有和解的可能了。」
我可以將過往無數歸于釋懷,唯獨沈園,沒可能。
當年她婚內出軌,被情人唆使掏空了我父親的家業,還生下了情人的孩子。
我始終想不明白,這一切的一切,沈園是怎麼能做出來的?
想不通,放不下,每次一想,錐心之痛。
怎麼算,沈園都是殺死我父親的兇手。
我不合時宜哽了聲:「和她的母女情分,早在當年就已經一刀兩斷,若虧欠了她的生養之恩,下輩子當牛做馬再還。」
這一生,絕無和解的可能。
「我不會勸你。」妙塵師父輕拍了拍我的手,「人來一世,是苦居多,拿起放下,自在就行。」
我雙手合十虔誠打坐,心境遂歸于平靜。
和師父告別后,出了禪房才見天色鴉青,有風雨將來。
山上春寒,我被遙遙而來的山雨攔在寺門前,索性站在廊下等雨停。
風自林間穿梭過,滾滾山雨喧囂不息,幽長的石階下有人撐傘走來。
程息梧就立在雨里,傘檐雨簾垂落,他一臉倦容。
這會兒剛過八點,瞧著,他昨晚大抵是沒睡好。
我緘默片刻,鬼使神差不正經地問:「你也來拜佛?」
程息梧抿著唇,不說話。
偶有雨絲飄入廊下,他騰出一只手撥開我垂在兩側泛著水霧的發絲,指尖停頓良久。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