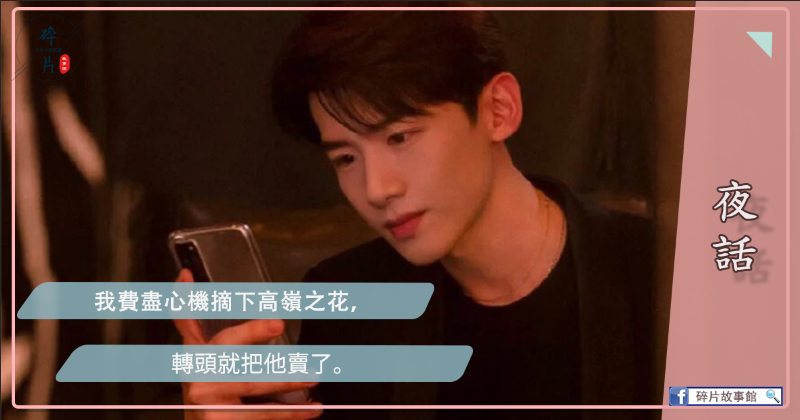《夜話》第8章
她不理解:「你在巴黎發展得那麼好,要回來當老師?」
我笑了笑:「當老師教書育人,多光榮啊。」
「就只是好聽點。」
她說得也沒錯,我留在巴黎,小提琴家的榮譽加身,名利皆雙收。
如果回來真的投身教育,就必須心甘情愿歸入平凡。
她還想勸,我笑著阻止:「我想家了。」
不知是不是心之所向,程息梧的身影遠遠自庭院穿過。
我抬了抬下巴:「也有點想他了呢。」
13
我能在陸映跟前嘴硬,在勞倫這,不需要。
她見過我初到巴黎時為一個男人要生要死的鬼樣子,陪我走過那段昏天暗地的日子。
「就是他?」勞倫順著我的視線看過去。
「除了他還能有誰啊。」
勞倫嘆了聲,不再多說。
把她送回樂團暫住的酒店,我又和昔日同事做了告別。
從酒店出來時,已臨近傍晚。
市井長巷,忽就覺得,其實這世界很大,也很空。
一時之間,竟不知道該往哪兒走。
程息梧的電話打進來時,我還站在路邊發呆,詫異地問他:「你怎麼知道我的號碼的?」
很好笑,明明見面后連包養協議都簽了,我和他卻陌生得連電話號碼都沒有交換過。
「在哪?」他懶得回答。
「在外面見朋友,有事?」
電話那頭他有一會兒沒說話,再開口,語氣明顯更冷了:「報地址。」
這幾年下來,程息梧的脾氣肉眼可見地暴躁了許多。
應該是,只對我沒什麼耐心。
我無奈地報了地址,他很干脆便掛了電話。
他沒說來,我卻還是知道他會來。
不到二十分鐘,程息梧的車開到跟前:「上車。」
我本能地坐到了后座,視線越過駕駛座的椅背,落在他掌著方向盤的手上。
ADVERTISEMENT
袖子隨意挽起,露出半截的修直小臂,手腕骨節弧線漂亮。
我可喜歡他這雙手了,當年為了牽上,費了好大勁。
「去哪?」我轉開眸光看向窗外。
程息梧一個聲都沒給我回。
就很離譜,氣兒比我還大。
沒開多久,他熄火停車,帶著我走進一個很雅致的私房中餐廳。
他應該常來,餐廳經理親自接待。
在菜上桌之前,程息梧和他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直接把我當空氣晾著。
直到菜上來,經理才離開。
我并不在意,拿起筷子剛準備夾菜。
程息梧涼涼地嘲諷道:「還知道筷子怎麼用嗎?」
這一路上都沒搭理我,現在終于憋不住了。
我著實被他氣笑:「能好好說話不?」
雖然在國外多年,但不至于連筷子怎麼用都不記得,他明顯就是在我跑到國外這事上過不去。
「不能。」
「……」
程息梧往后靠去,一只手搭在紅酒杯上,輕輕輾轉。
冷意極盛地說:「我說過,騙我你就死定了!」
「哦。」這話我記得。
主要是,我也沒騙他啊,喜歡他是真的,想和他在一起,也是真的。
不愿意過多解釋,無趣。
看他這憋著一股勁的樣,我就想逗他:「那你說說,想讓我怎麼死?」
程息梧抬眸陰森地盯著我,不搭腔。
我彎了彎唇:「欲生欲死?」
「閉嘴。」
他額角抽搐,忍無可忍地拿起筷子夾了一個蝦仁往我嘴里塞。
我笑得更歡。
似乎,他有些地方還是沒變。
至少在被我調戲的時候,他仍然很可愛。
14
離開餐廳,上車時我習慣性地去拉后車門。
手剛碰到車門把手,就被他按住了。
「坐前面。」
我沒什麼異議地轉身,程息梧卻沒有動,咫尺之間的距離,彼此的衣衫摩挲聲聲。
ADVERTISEMENT
他人高,擋住了身后大半的燈火,我整個人籠罩在他的陰影里。
這樣的氛圍之下,我的心頭莫名就生出了一股熱流。
想在這暮春晚上的街頭,擁抱他,雙手穿過他的腰把人抱得緊緊的。
就用一個擁抱,無聲訴說分開這些年的路。
可怎麼呢,始終沒辦法張開手。
我不禁暗暗自嘲,年年歲歲地成長,我也從那個勇敢熱烈的小姑娘,長成了怯懦膽小的大人。
他突然開腔:「為什麼決定不走了?」
吃飯那麼長時間話都不愿意說幾句,這會兒反而出聲了。
我的心思是有些卑劣的,故意氣他:「應該是我更喜歡用筷子吃飯吧。」
程息梧垂頭睨著我,半晌諷刺地勾唇:「你讓我好好說話的時候,有反省過自己是什麼鬼樣子嗎?」
「呃。」我反應過來,其實我也沒好好說話呢。
回去的路上,他更加不愛搭理我了。
車子一路開進地下車庫,我出于禮貌問道:「上樓喝杯茶再走?」
程息梧直接熄火下車,順帶從后備廂拿出了一個行李箱,比我先一步進了電梯。
「額。」我有點懵,他聽不出來我只是想客氣客氣?
還有,他拿行李箱去我家做什麼?
行吧,邀請是我發出來的,我也得認。
回到家,我殷勤地給他泡好一壺茶,坐旁邊干巴巴等著。
我想我已經表現得很明顯了,喝完茶趕緊走!
程息梧權當沒看見,垂下眼慢條斯理解開袖口:「我明天休假。」
「嗯?」所以呢?
「今晚不走了。」
說這話時,他把袖子往上隨意翻折,人也往沙發后靠去。
直直看過來的眸光,帶了點促狹的玩味。
分明就是說:「茶我喝,但我也不走。」
我不太確定地問:「你要搬來和我一起住?」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