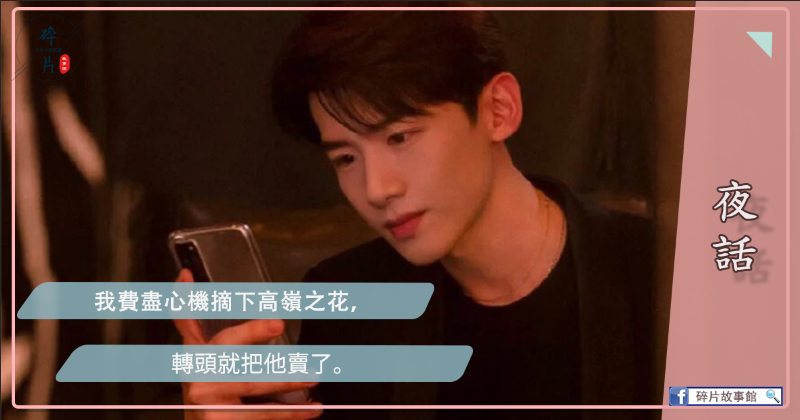《夜話》第7章
一陣沉默后,程息梧沒有走,反而拽過我的手,按著咬破的傷口。
他垂著眉眼,看不大清楚情緒,語氣依舊有點刺:「隋枝,你是想讓誰心疼呢?」
我掙扎了一下,抽回手:「我都不覺得疼,自然是不需要誰心疼的。」
論刺,我和程息梧,誰服誰啊。
注定是沒什麼愉快的收場的。
程息梧看著空了的手頓了頓,爾后勾了唇角。
像是自嘲般,無聲笑了。
他走后,我也乏得很,沒力氣去收拾那一室的狼藉,直接躺下了。
早上迷迷糊糊被客廳里哐哐當當的聲音吵醒,出來一看,原本杯盤垃圾雜亂的客廳,已然被收拾得干干凈凈。
保潔阿姨提起垃圾離開。
「起來了。」陸映抱著一包薯條坐在沙發上,見我起來了,撈起遙控器打開電視。
視線在電視屏幕上,不停地換著臺,「昨晚挺累的吧,來,坐下來歇歇。」
她拍著身邊的位置向我發來熱情的邀請。
我看她那裝得無波無瀾的樣,明晃晃就一個意思:快來,和我說說昨晚的盛況。
「把你腦子里那些黃色的東西都清理掉,什麼事都沒有。」
「啊?」陸映秒破功,跳起來指著我控訴,「小枝枝,咱還是不是姐妹了?你現在都能騙我了。」
我很無辜:「哪看出來我騙你了?」
「我來的時候才看見程哥的車離開,敢情你們昨晚蓋著棉被談了一夜的人生理想?」
12
「他一直沒走?」
我驟然就有點難受,人啊,就是傻。
反正我又不會心疼,他在那耗什麼勁兒呢。
「難道他是在車上待到天亮的?」陸映一臉驚訝,問道,「不是,你們什麼情況啊?沒和好?」
我也不知道怎麼和她解釋,拉開抽屜把昨晚簽的那一份協議拍到桌上。
ADVERTISEMENT
「自己看。」
陸映看得眼睛都直了:「哇塞,你們多少歲了,還玩這麼幼稚的?」
我無奈地嘆氣:「沒辦法,他較真了。」
「那你就陪著他鬧啊?」
我頓時失語,心虛地起身去洗漱。
陸映慢悠悠晃到洗手間門口:「其實,你也沒真的放下吧?」
她一臉「放下的話你陪他瞎鬧啥」的表情,我慢吞吞刷著牙,沒吭聲。
「仔細想想,也挺好的。」陸映倚在門邊,長吁短嘆,「你們兩個都是驕傲到骨子里的人,明明誰都沒放下,但就是誰都不肯先低頭。」
她突然拍手,痛心疾首地說:「造孽啊。」
我被她逗樂。
「你還笑得出來,小沒良心的。」
「我怎麼沒良心了?」我很無辜。
「當年你剛走前幾個月,程哥找你都找瘋了,隔三差五來堵我問你在哪,他哪知道你連我都沒聯系。」
說著話,她用眼神直瞪我:「我覺得程哥對你,不像是假的。」
毛巾撲在臉上,我悶悶地說:「可能是我追著他跑太長時間,人一下子不見了,他反而不習慣了。」
雖然不想承認,但在旁人眼中,我真算是程息梧的舔狗。
被舔的時間長了,他難免會形成習慣,正常。
「才不是,要真不喜歡,他能這麼多年連個戀愛都不談?」
我下意識問:「他和顧明瑤后來沒在一起過?」
「怎麼可能。」陸映極其不屑地說,「就算沒有你,也沒顧明瑤什麼事。」
「哦。」我還以為,他們是后來分開了呢。
「顧明瑤吧,就是腦子不好使點,人不壞。」
我揶揄笑道:「難得啊,你竟然為她說好話。」
以前陸映沒少和顧明瑤掐架,兩個人少時便認識,愣是沒成為朋友,吵個沒完沒了。
「咱是講道理的人。
ADVERTISEMENT
」陸映吧唧著薯片,叨叨,「她打小跟在程哥后面跑,就是受不了你搶走了她的息梧哥哥,鬧一鬧,知道自己沒戲,也就死心了。」
「你出國的第二年,她找了個小白臉,整天膩膩歪歪的,沒多久就結婚了。
「哦,程息梧他媽媽還認了她當干女兒來的,關系一直都很好,但她確實沒和程哥在一起過。」
我聽出了陸映的用意,笑問:「怎麼,你也勸我和他復合?」
「切,我艸不勸你,你就仗著程哥放不下你,繼續作吧。」
「你這話我不認同。」我拿下臉上的毛巾。
不著調地說:「哪有什麼放不下,連個手都不讓我牽,偷親他一下能幾天陰著臉不理我,嫌棄死我了才是真的。」
陸映切了聲,吐槽道:「你當時那德行,誰都以為你只是走腎不走心。」
我盯著鏡子里滿臉是水的自己,有些恍惚。
這張眉目溫淡的臉,再也難以和記憶中曾經那個飛揚肆意的自己劃上等號。
我的勇敢,怎麼就成了走腎不走心?
這個浮躁的世界,人心似乎也捉摸不定了呢。
午后,我去接勞倫出院。
她悶壞了,搭著我的肩單腿著地一蹦一跳拐到庭院后,急急催我:「煙,枝枝兒,給我煙。」
我把煙遞給她,笑道:「怎麼,她們來看你,沒讓你抽?」
勞倫一臉幽怨:「她們故意的,壞死了。」
狠狠抽了幾口,她心滿意足地摟著我的脖子親了一口:「枝枝兒對我最好。」
「咦。」我嫌棄地抹了抹臉頰不存在的口水。
過足了煙癮,她才問:「你真的不跟我們一起走嗎?」
「嗯。」我半開玩笑道,「正在接觸國內的樂團,如果沒人要,再不濟也能當個音樂老師不是?」
在法外交響樂團待了幾年,有這個機會回來,倒也是個好事。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