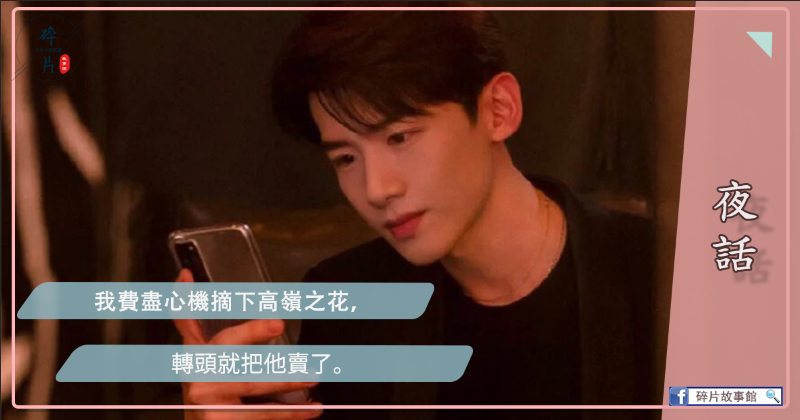《夜話》第6章
我嗆得眼眶都紅了,眸子狠狠剜他。
「游戲而已嘛,再說了,你剛才都承認自己想睡他了不是嗎?」
我可真謝謝你嘞。
人嘛,有一個損友是正常的,但有一群,那就是災難。
譬如現在,在陸映拋出這個爆炸的問題后,所有人都跟打了雞血似的,目不轉睛盯著程息梧。
處在風暴中心的人,隨意地靠在沙發上,半撩眼皮慵懶出聲。
「你們可以走了嗎?」
所有人:「???」
謝放大喊:「程哥,你別玩不起——」
「我現在就想和她睡覺。」
10
人群在哄堂大笑中散去。
謝放臨走時,還賤兮兮地來了一句:「程哥,槍就是得多練,你越不練,就越不中用,加油!」
我的太陽穴突突地跳,尷尬得要命。
「砰」一聲,程息梧直接就把門摔上了。
站在門外的謝放臉應該是磕在門板上了,疼得在外頭鬼哭狼嚎。
很快就被誰給拽走,沒了聲音。
我刻意忽略掉程息梧的存在,轉頭看向一片狼藉的客廳,無奈地嘆了聲。
得,做衛生都能要了我半條命。
程息梧低沉的聲音冷不丁響起:「從哪里開始?」
我一愣,腦子有點不好使地問:「開始什麼?」
玄關處的燈光不太明朗,程息梧的面容沉在微光里,狹長眼眸氤著毫不掩飾的嘲諷。
「不是要包養我?」
嗯,這話我說過。
「然后呢?」我額頭上寫滿問號。
程息梧突然邁開長腿,一步步靠近:「滿足雇主的要求,是我的本分,請問,服務從哪里開始?」
說話間,他修長的手指正慢條斯理地解開襯衣的紐扣。
我傻眼地看著男人近在咫尺地裸露結實胸肌,耳垂瞬間便燒了起來。
ADVERTISEMENT
別說,身材還挺有料。
「你說話就說話,別脫衣服啊。」我趕忙出聲阻止,這純純就是怕自己被美色耽誤了。
程息梧居高臨下睨著我,挑聲譏笑:「不脫衣服,你怎麼玩我?」
臥槽!
你他媽有毒吧!
我承認,多年前我放蕩不羈,野性難收,的確說過想玩他的話。
可這都過去這麼久了,他還能記仇到現在?
「行吧,我道歉,不該輕薄你。」我是有色心沒色膽,口嗨比誰都溜,真要真槍實彈地上,趕緊認慫吧。
「不接受。」
程息梧冷冷地掀唇,越發靠近了些,我退無可退,背抵在吧臺上。
一呼一吸間,交纏上他的氣息。
「程息梧,你他媽真的有病吧,都說了,我那是開玩笑的。」
沒想玩他,也沒想包養他!
程息梧雙手撐在把臺上,把我圈在一方之地,低垂著眼簾,眸色很深。
「隋枝,我是認真的。」
我的大腦有些轉不過來。
他要是說當真,那還可以理解,他說認真,就有些令人費解了。
認真什麼呢?
我不愿意細想,裝不懂,沒個正經地調侃:「程醫生就這麼上趕著求包養?」
原以為程息梧又得氣死。
沒想到,人家表情自然、半點不羞恥地說:「這麼好賺錢的行當不多了,我可以的。」
我人都傻了。
這特麼還是我認識的那個君子端方的高嶺之花?
程息梧好整以暇:「初次上崗,服務不周,我還可以給你打個對折。」
我徹底凌亂了,小心翼翼地問:「這些年,你到底受了什麼刺激?」
太騷了,這誰招架得住?
也不知道我這個問題到底是戳到了他哪一點,他不耐煩地扯了扯唇,語氣帶點兒嘲諷:「金錢交易,談心就免了。
ADVERTISEMENT
」
我一陣語塞,心里無端地窒息。
分開這些年,歲月的長河把我們隔開在兩岸,中間流淌的,是我們無法跨越的愛恨嫌隙。
我們誰都沒有走遠,但誰都,不愿低頭。
11
一定是這晚的燈光迷離,我一時鬼迷心竅。
竟真的默認了這樣不正常的關系。
程息梧是帶著目的來的,我瞠目結舌地看著他從西裝口袋里拿出一紙合約。
儼然一副公事公辦的姿態,簽了名字還不夠,禮貌地問我:「有印泥嗎?」
這玩意我哪有,遂搖了搖頭。
程息梧的目光在我的唇上停頓半秒。
我還沒來得及思考他到底想干嗎,男人微涼的指腹便已經輕輕摩挲過我的唇。
手下溫柔,舉動曖昧引人遐想。
我不由緊張地挺直脊背。
「這個也可以將就用用。」而他眉目漠然,用沾著我口紅的指腹,按在紙上「程息梧」三個字上。
我:「???」
你要用我的口紅你倒是直說,我把整根口紅都給你。
非要用這麼讓人小鹿亂撞的方式?
我暗自腹誹,想找口紅,又不記得放在哪。
程息梧冷淡地盯著我,眉峰凌厲,像是在監督人。
那股子冷漠勁,完全是不用講情分,單純肉體交易的態度。
我頓感心煩氣躁,狠了狠心,在指尖上咬了一口,按下手印。
「可以了吧?」我看著指尖冒出的殷紅血珠,眉頭都沒有皺一下,「你可以走了。」
程息梧抬了抬下頜,在明晃晃的燈影里,沉默。
「還有事?」我悠悠輕笑,學著他的話術,道,「既然我是雇主,今晚不用服務。」
話出口,我自己先樂了。
也不知道哪兒好笑,就是覺得過于荒唐。
說出來都沒人相信,分手多年的戀人,多年后再一次相遇,卻簽訂了最膚淺的肉體關系契約。
一個敢提,一個敢答應。
兩個瘋子。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