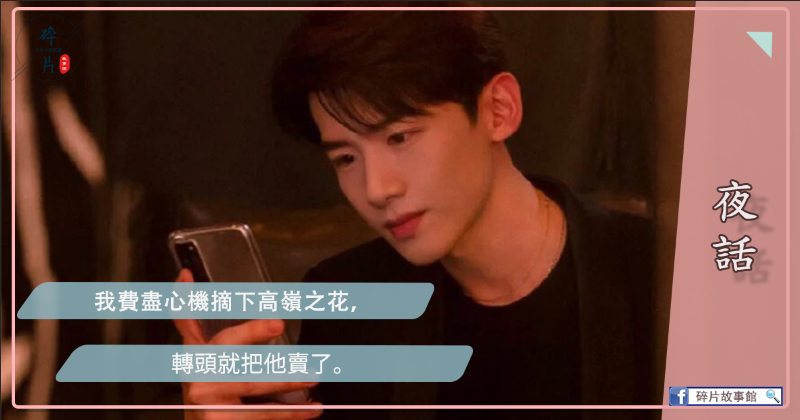《夜話》第4章
」
顧明瑤眼神鄙夷但說出的話卻十分豪氣:「就這點小錢啊,阿姨不給,我都能給你。」
我白了她一眼,只覺得她多少有點毛病。
誰知道過了幾個月,他媽真就給我打了一個電話。
在這之前,我跟隨沈園在各個宴會上,是見過她幾回的,人挺溫善,可可愛愛一富太太。
她問我是不是在和程息梧談戀愛,我說沒有。
那會兒發生了一些事,我已經決定放棄程息梧,連承認和他談過戀愛的底氣都沒有。
但是程太太的腦回路似乎和常人不同,她篤定地說:「那就是分手了。」
說完嘆了好長一口氣:「分手了女孩子肯定比男孩子吃虧,聽明瑤說你要五百萬分手費,要不你給阿姨打個折?」
我無了個大語,再加上那天心情極低落,隨口敷衍了兩句就掛了電話。
離譜的事來了。
第二天顧明瑤就甩給我一張兩百五十萬的支票:「程姨給你的,她希望你能好好用這筆錢,好好生活。」
我直接就樂了。
她這人真能處,要錢真的給。
思及此,我淺淺彎了唇:「阿姨,你沒發現那張支票,我沒兌過?」
「啊?」她錯愕了一下,懊惱地跺了跺腳,「哎喲,我真沒發現,錢太多了,那筆小錢我都沒注意到。」
我被她可愛到,抿了抿唇:「阿姨,我送你出去吧。」
出劇院的路上,她念叨著:「你這孩子,阿姨給你的零花錢,怎麼不拿著,這些年過得挺辛苦吧?」
她安慰地一下又一下拍著我的手,我不太習慣這親昵的接觸,又不忍拂她的好意。
隨她了。
「瘦了,人也消沉了。」她幾次嘆氣,「阿姨記得你以前是個明媚活潑的孩子,討喜得很。
ADVERTISEMENT
」
我心頭倏然被刺了一下,臉上保持著得體的微笑:「阿姨,人都會長大的嘛。」
到門口,她這才放開我:「息梧來接我了,要不要和他見見?」
我順著她的視線看去。
暮春的晚上,微雨茫白,柏油路濕漉漉的,臺階下停了一輛黑色賓利,車窗緩緩降下,年輕男人一只手搭在車窗上,側臉驚艷卓絕,氣質矜冷。
在他有轉頭向這邊的趨勢時,我收回視線避開他。
「阿姨,已經見過了,不用再見。」
和她說了再見,我轉身往劇院里走,隱約能感覺到遠遠落在我背后的那道目光。
冷冽又灼人。
7
云層疊疊如浪如海,薄光穿透禪房窗紙,溫柔攀附在肩頭。
「你有兩年沒來了。」盤腿坐在蒲團上的妙塵師父眉目慈善,把茶盞輕推到我跟前。
我垂首謝禮,雙手端起:「這兩年都沒回國,被事兒絆住了。」
走了七年,前五年我每年都會回來一趟,最重要的行程就是到寺里上香。
「去給你爸上過香了嗎?」
「上過了。」
「嗯。」她細瞧了瞧我,微笑道,「比前幾年平和了。」
「想開了。」我抿了一口茶,淺淺的甘香在唇齒蔓開,回味悠長。
她柔聲勸導:「人死不能復生,萬般皆是命,你是有慧根的孩子,定會苦盡甘來。」
「謝謝師父。」
禪房靜謐,只有矮桌上煮著的茶水發出低低的沸騰聲。
她忽然輕聲問:「那他呢,放下了嗎?」
我愣了愣,才反應過來她說的是誰。
我父親是個五大三粗的暴發戶,但他這人特迷信,拜佛搶頭香的事沒少干,特別虔誠。
在他的熏陶下,我雖然性子野,在外頭張揚得不行,跟著他到了寺院,也乖乖拜佛上香。
ADVERTISEMENT
他那會兒還想慫恿我去拜妙塵師父,做她的俗家弟子來的。
我追程息梧那會兒,厚著臉皮拉他來過一趟寺里。
那次我偷偷在佛前許了個愿,誰也不知道。
也挺神奇,回去后沒多久,我真和他在一起了。
還特意拉著他來還愿,他瞧著我正正經經的樣子,還難得地笑了。
來來回回,妙塵師父便也認得他了。
后來我父親去世,我花錢在寺里給他捐了功德,讓他的骨灰盒留在寺里吃香火。
我每年回來給他上香,都會在妙塵師父這待上一天半天,難免就會提起程息梧。
由最初的痛心到后來的風輕云淡,我用了五年時間。
我平靜地啟唇:「都過去這麼多年了,早放下了。」
妙塵師父目光柔和看了我半晌,洞悉一切地自如:「他這幾年每年都會來兩趟,風雨不阻。」
我訝然抬頭,想是茶有后勁,唇齒間有了苦味。
師父轉著指間佛珠,輕嘆息:「那孩子該是有些執念的。」
我不吱聲,她看了我一眼,嘆息:「愛如逆風執炬,必有灼手之患。」
話落下,她閡上眼入定。
禪房歸入寂靜,我盯著矮桌上熱茶升起的白煙靜默許久,起身躬了躬,離開。
離開時已近黃昏,剛出寺門,一眼就看到了那抹熟悉的身影。
天邊云蒸霞蔚,半人高的爐鼎白煙繚繞,百年銀杏枝繁葉茂,垂掛著數不盡的許愿香袋。
那人簡單的黑褲、白襯,穿著薄薄的長風衣,迢迢風姿玉骨。
我緩步走近,笑著揚聲:「來堵我的?」
程息梧側過頭瞥了我一眼,依舊是那副嘲弄的語氣:「挺能躲啊,躲了七年,終于不躲了?」
我有種說不出口的難過。
師父說他年年都來,我也回來過許多趟,并沒有刻意躲,還真一次沒碰上。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