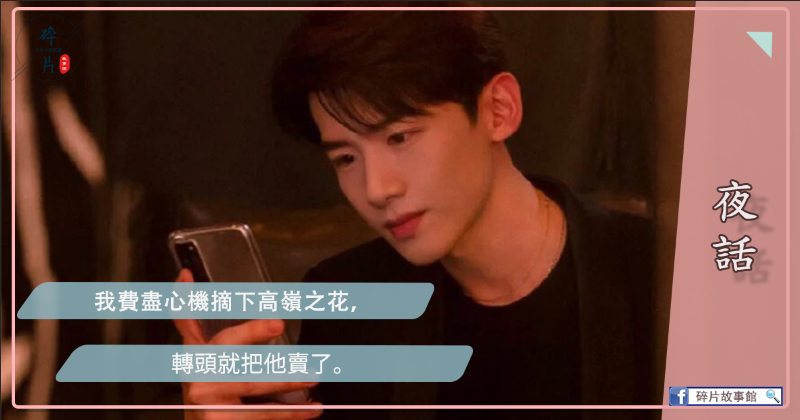《夜話》第3章
」
「隋枝。」
暮色四合,他的聲音混著風低沉隱晦。
我識趣地斂了笑,靜等著他說下去。
雨絲紛紛揚揚裹了他一身,出聲沉涼:「既然不愿意跟她走,那就跟我吧。」
話入耳,我驚得手一抖,煙灰簌簌散落。
「程息梧。」我被逗笑,「你腦子沒毛病吧?」
他的目光緩緩落到我臉上,顏色淺淡的眸子冰冰涼涼沒半點溫度。
「你不是那麼喜歡錢嗎?」帶了點譏誚的冷笑,「我有。」
這話扎扎實實擊中我的軟肋,往事一幕幕浮現,我心頭的火剛又冒起來的苗頭,瞬間湮滅無聲。
我溫淡點頭:「是,你沒說錯。」
涼風撲在脖頸,我垂下頭看著指間的煙被碾壓扁平,心平氣和:「程醫生,我想你該去看看心理醫生。」
我自問這些年我已經能做到心靜如水了,還是被他這一出給弄得不知所以。
本來就沒多少情深意重,隔了這麼多年,早該偃旗息鼓了。
他在鬧什麼勁?
風聲迂回,他半自嘲半認真:「我有病,你能治。」
「……」我啞了聲。
手機鈴聲不合時宜地叫囂,我轉過身去接。
專車師傅在不遠處打著雙閃,橙光閃爍,我深深吸了口氣。
「過去的我都忘了,也沒想過回頭,治不了你。」
我無數次咬緊牙關走過來的路,沒有回頭看的打算。
程息梧緊緊盯著我,半晌后,情緒撕開一個口子,陰沉扯唇:「真狠吶,隋枝。」
5
我笑問他:「哪狠了?」
程息梧忽地低笑,諷刺道:「說走就走,不能說你狠,還得夸你瀟灑?」
他這些年是真變了,棱角尖銳,不似以前溫和。
「那是,我人美且狠,謝謝夸獎。」他越氣,我就越不著調,「我當年甩了你,你現在用包養來折辱我,咱倆扯平了。
ADVERTISEMENT
」
專車師傅等得不耐煩了,直按喇叭催促。
我頭也沒回地揚了揚手:「程醫生,再見。」
上車離開時,后視鏡里映著程息梧的身影,他迎風站在暗夜里,沉默不動。
我看著窗外,心緒難平。
多年前,我是那個棱角鋒芒畢露的人,他待人溫柔,雖總有距離感,但極致的好教養,他從不曾讓人難堪。
就是我瘋狂追他的那一段時間,做了很多出格的事,他都未曾有過片語反感。
所以那時候我自我感覺挺良好,感覺他也是喜歡我的。
殊不知,那僅僅是因為他良好的修養,君子端方,克己復禮,連憎惡都抑制了。
可是,我分明記得,他也曾回應過我的啊。
恍惚間,記憶拉開序幕,回到那個燒著暗火的寒夜。
在我堅持不懈追了他一年多以后,某個下著大雪的冬夜,我和舍友跟著幾個學長偷跑去酒吧鬼混回來,在校門口和他碰了個正著。
天寒地凍,路邊高高的路燈上覆了一層雪,燈光朦朦朧朧。
他肩上、發上落了雪花,似乎等了有一會兒了。
我被他按在結了冰碴子的燈柱上,人都傻了,呼呼撕扯的風聲里,依稀聽到他低沉的聲音:「就是這麼喜歡我的?」
當時我喝了酒,腦子不大清醒,也沒反應過來他當時是在氣我和想追我的學長走得太近。
而且他距離太近,我心跳怦怦然,一個勁傻乎乎地點頭:「對啊,我喜歡你,喜歡得要命。」
他明顯愣了愣,氣兒也消了。
雪花紛紛揚揚落下,他俯頭靠近,唇畔擦著我的耳垂,低語:「隋枝,敢騙我你就死定了。
ADVERTISEMENT
」
后來很長時間,我想起這個晚上,只記得天很冷,但是我的心卻燒得不像話。
整顆心,都是滾燙的。
我以為,那是我們的開始。
誰知道我把一顆燒得火熱的心捧給他,卻被澆了個透心涼。
事實證明,一個擁有所有世俗五情六欲的人,妄想攀上高潔清雅的高嶺之花,是天方夜譚。
我被狠狠教育了。
傷心勁過后,只剩下心如死水。
程息梧拿出包養的話來羞辱我,我不生氣。
只是有點難過罷了。
6
在國內最后一場演出結束,觀眾離席,我抱著小提琴往后臺走。
「小枝?」身后女聲驚喜。
我停下腳步,回頭,后邊走過來一個打扮時髦的中年女人,瞧著端莊,表情卻雀躍似年輕女孩。
「真的是你,剛才在臺下時我就覺得很像。」她熱情地拉住我的手,上下打量,「哎喲,這漂亮的小模樣,我就說沒認錯。」
我微微訝然,怎麼也沒想到,遇上前任也就罷了,還能遇上前任他媽。
而且,這位太太還十分之熱情。
「你都不知道,剛才我在臺下和朋友說,拉小提琴的姑娘和我兒子交往過,她們可羨慕壞了。」
我忍俊不禁,這是什麼奇妙媽媽。
她日常嫌棄自己的兒子,嘟囔道:「息梧那沒眼力見的,和你分手是他的損失。」
「阿姨,您說笑了。」
「沒說笑,你是個好孩子。」她愛不釋手般撫著我的手,欣慰萬分,「我就知道,你肯定不會辜負阿姨的期望,一定可以有出息。」
我想起一段舊事。
那晚程息梧把我堵在校門口后,我便滿心歡喜和人張揚,自稱自己是程息梧的女朋友。
風聲傳到顧明瑤的耳中,她氣哄哄來找我:「不要再纏著息梧哥!」
我當時沒把她看在眼里,嘚瑟地隨口一說:「可以啊,那你讓他媽給我五百萬分手費。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