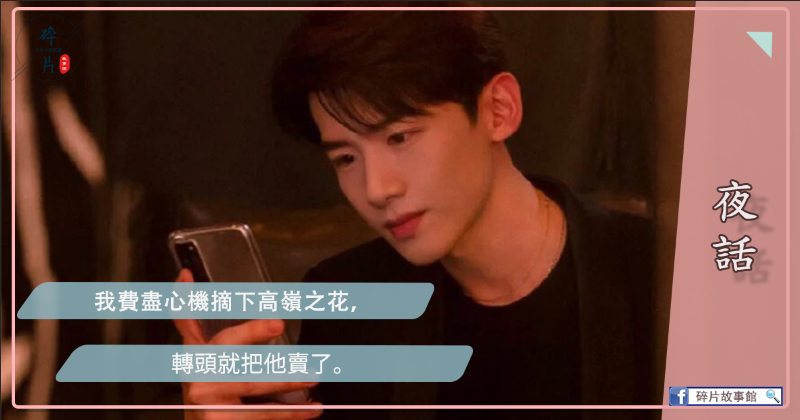《夜話》第2章
我倚在辦公桌旁,盯著他在玻璃柜里翻動的手,皮膚冷白,能瞧見凸起的青色血管,指甲修剪圓潤的五指清瘦修長。
這人渾身上下,都透著無比優越的清貴氣度。
心情有些復雜,不由玩味地啟唇:「程醫生不用哄人?」
按照顧明瑤以前的性格來看,被我弄哭了,不得纏著程息梧求安慰?
現在這麼好哄了?
程息梧一點反應都沒有,面孔冷冷清清,沾著消毒水的棉簽直接懟到我眉間的傷口上。
刺痛感令我皺了眉,鼻息間除卻消毒水的味道,還涌入了他身上自帶的清冽淡香。
我暗暗長吸氣,如同在沙漠行走許久的旅人,貪婪地吮吸天賜甘露。
心里有什麼情緒壓都壓不住,即將噴發而出。
「打架?」冷淡得要命,像詢問,更像譏誚。
我剛才還在慶幸,相逢平淡如水也挺好,沒想到,是我想得太美。
「嗯。」我坦坦蕩蕩,「有什麼好奇怪的,以前我也常打。」
你又不是不知道。
程息梧顯然沒想到我能這麼理直氣壯,靜了一瞬。
「真有能耐。」這回譏諷是直白的。
凄凄冷冷的風吹在脖頸,我斜著眼睛瞧著他薄冷的眉眼,心尖的刺,忽地冒出頭。
我溫和隨口一句:「那有什麼,我當初甩你的時候也很有能耐。」
3
戳別人的痛點的結局就是,他手中的棉簽一點不客氣地重戳進我的傷口,我不想認為他是手抖,肯定是故意的。
這男人,對誰都是一副君子端方的模樣,只有我知道,他小氣得一匹。
我是被程息梧趕出來的,他像是動了氣:「死性不改。」
走廊里燈光刺眼,我瞇了瞇眼站在緊閉的門外。
ADVERTISEMENT
胸腔悶悶的,再遇仍有后勁啊。
第二天被通知到警局補口供,離開時已近傍晚。
一出門口,就遇上了等在那的女人。
看得出來,這些年她過得不錯,全身上下整一套奢牌高定,精致保養過的臉看不出太多的歲月痕跡,溫溫柔柔的模樣,盡是歲月靜好。
她迎上來:「小枝。」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我微微側身躲開她伸過來的手。
我隨行法外交響樂團回國演出的消息,沈園是知道的,她聯系過我幾次想見面,我拒絕了。
沒想到,她的消息還挺靈通。
察覺到我的動作,她尷尬地收回手:「你陳叔在局里工作,他看到你了。」
她說的陳叔我沒什麼印象了,也不想打聽。
我冷淡地問:「找我做什麼?」
許是我的冷漠勁兒太明顯,沈園有點不知所措:「媽媽就是想看看你。」
我勾起唇好笑地看著她,毫不掩飾地譏誚:「哦,我還以為你忘了呢。」
她如今家庭美滿幸福,不記得有我這個女兒很正常。
「小枝,媽媽怎麼會忘,聯系過,可你以前的號碼都不用了,我……」
「別說了。」解釋這些,有什麼意義呢。
沈園悻悻地打住,過了一會兒又說:「你回來住哪兒?要不回家住吧。」
我壓下心頭煩悶,竭力平和道:「那不是我家。」
「小枝。」
「你回去吧。」
沈園難掩傷心,默默站了幾分鐘才往車子走。
豪華商務車門滑開,一個梳著中分、穿小西裝的小男孩撲到她懷里,沈園慈愛地接住他上了車。
車子緩緩遠去,我收回目光,猝不及防察覺眼眶有點發熱。
眨了眨眼壓下那股熱流,掏出煙點著,風掠過唇上煙,那點紅光在風中灼灼燃燒。
ADVERTISEMENT
我放空地看向對面的車道,后知后覺地發現,似乎那輛黑色的賓利在那里停了好長時間了。
車窗緊閉,很難窺探里面是否有人。
早春天色漸沉,灰蒙蒙的天細雨翩然落下,白煙從唇齒間逸出,消弭于春風。
許是正值下班高峰期,打車平臺上的訂單遲遲沒人接。
我向來慢性子,細雨如織,我仍能不緊不慢點上一根煙,悠哉等著。
幾分鐘后,路對面黑色的賓利躁動地沖出去,在百米開外猛地掉頭。
剎車聲在無人的傍晚尖銳刺耳。
車窗搖落,我在漂浮起的煙霧里微微瞇了眼:「程醫生,這麼巧?」
4
程息梧目視前方,側臉輪廓在早春薄薄的暮色里,勾出清寒的輪廓。
「上車。」
沈園來找我,這不意外,他來,倒真有點意思。
我好整以暇地倚著路牙子,沒動。
「你也有事?」我和沈園說話那會兒,他的車就已經停在那。
都看到了吧。
程息梧緩緩側過臉,臉色冷淡,欠缺情緒,視線從我的眼睛掠過,又移開落在不知名處。
唇邊弧度淺淺:「也沒多大出息。」
「呃……」我偏了偏頭,眼睛里未散的紅暈到底是暴露了情緒。
讓他逮著嘲諷的機會。
我撣了撣煙灰,問:「程醫生這麼閑?」
這麼多年沒見,他這人是越發難懂了。
倒還是當年高山白雪難攀的姿態,但怎麼瞧,都能讀出來一絲別扭的情緒。
不就那一段嘛,當時追他轟轟烈烈、人盡皆知的是我,丟人的也是我,我現在都能坦然跳過,他反而有刺。
雨絲交纏愈密,程息梧沒等到我上車,耐心耗盡,下車時略顯暴躁地甩上車門。
頭上移過來一把雨傘,他舉著傘,自己卻站在雨里。
心里的漣漪起了又去,我漫笑調侃:「怎麼,近一點我能吃了你啊。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