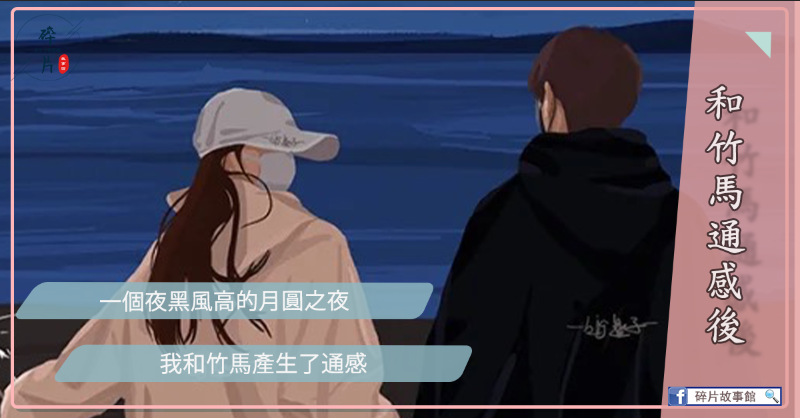《和竹馬通感后》第5章
有時候戳的手心,多數時候是臉頰。
專屬實時通信方式,催促我趕緊理他。
其實他一大男人整天戳自己臉挺好笑的,但我還是狠心咬牙沒回。
這時他又會咯吱我。
雖然是在他自己身上動的手,但他不怕癢我怕啊,往往這時候我只能繳械投降。
和江景斗智斗勇的這段時間,社團那位自來熟的陸學長開始追我。
宿舍蹲我,教室堵我,還總借社團活動和我湊在一起,又是送花又是送小禮物,手段層出不窮。
在我第三次明確拒絕后,他終于有些氣餒:「一點機會都不給嗎?」
我笑著搖搖頭。
他苦笑一聲:「其實江景給我發過消息,他說他這麼帥都追不上,我就更別想了。但我以為你倆這麼多年都沒在一起,那我肯定還有機會。」
他問我:「其實你喜歡江景的吧?」
「不喜歡吧。」我回。
他又道:「那你怎麼不直接拒絕他?」
「……」
我竟無言以對。
這段對話又被江景聽去,到他嘴里儼然成了「我對他有點意思」。
我索性直接拒絕:「沒意思,別想了,我倆也不可能。」
也不知是不是報復,當晚,那萬年不通一次的視覺再度閃現。
江景當時正在換衣服,呈現在我眼前的是他半露不露的緊實腹肌。
他估計也很蒙,但很快他把衣擺又往上撩了一點。
該說不說,還挺勾人的。
我雖然嘴上抱怨著「趕緊把衣服放下,丑死了」,但視線總控制不住地一瞄再瞄。
視覺持續 30 秒,以江景緩之又緩穿好那件 T 恤的動作告終。
自這次起,江景一換衣服必通視覺,簡直就跟定點打卡似的。
ADVERTISEMENT
要不是知道江景也是通感的受害者,我簡直要懷疑他就是幕后主謀。
這一天天的,色誘我呢?
江景也很費解,還找我說理:「是不是你在背后操控呢,你要是饞我身子就早說。」
我損他:「謝謝,并沒有什麼看頭。」
他懷疑人生:「你對我就沒有一點世俗的欲望嗎?哪怕一丁點?」
「吃點溜溜梅吧你。」
就在我以為我和他之間的通感徹底沒救的時候——
江景突然找上我,雙眼放光:「我好像知道通感是怎麼回事了!」
「可能是小花!」他說。
10
事發當晚,江景擼的那只貓就是小花。
小花是江景撿來的。
高考前,他隨爺爺奶奶去廟里為高考祈福,在山腳下看到一只臟兮兮的瘦弱小貓,當時頭頂烈日,小貓卻躲在墻后的榕樹下瑟瑟發抖,腹間清晰可見的肋骨仿佛都要抖散架了。
江景動了惻隱之心,就把它抱回家養著。
由一只細瘦伶仃的難看小花貓,養成一只胖乎乎、毛茸茸的神氣小花貓。
而江景之所以有此一想,全因為他想起在撿小花回家的當晚做的一個夢。
夢里有一位老神仙,幻化成小花的模樣,說感謝他救了他,可以幫忙實現他的愿望,問他有什麼需要。
夢里的江景沒許愿,夢外更不可能對著一只小花貓許愿,只把這當成一個尋常的夢,做過就忘了。
直到舍友在他面前提起一個金斧頭銀斧頭的故事,江景才想起還有這樣一個夢。
繼而聯想到通感,并找上我。
我有點不敢信,我覺得這比流星遂愿還扯,但江景很篤定地點了下頭:「信我。
ADVERTISEMENT
」
他說從視覺的閃現開始,他就有種預感,通感不是那種機械式的遂愿,更像是有什麼靈性的東西在背后操控。
我不得不承認這話有道理。
通感像是為了加深我和他之間的羈絆存在的,通感這段時間,我了解到江景的很多面,是以前的我不可能了解到的。
江景說:「通感好像在幫我追你。」
我腦子霎時閃過一些畫面,一些光是想想就要羞紅臉的畫面。
我有點被說服,道:「那我們這周回家,問問小花?」
他剛點頭,手機響起來。
接過電話的江景告訴我:「我媽打來的,她說小花丟了。」
我驚愕地瞪圓了眼。
這下不用等到周末,我倆當天就麻溜滾回了家。
到家前,我和江景先在小花最后出沒的地點找了許久,毫無蹤影。
天色已晚,江景商量說不如先回家制作尋貓啟事,我點頭,開始在小區業主群編輯尋貓文案。
江景家冷冰冰的。
江阿姨丟了貓,很自責,拉著剛下班的江叔叔還在外面找。
江景著我直奔臥房,我晃晃手機:「我媽說飯快做好了,待會兒你領著叔叔阿姨來我家吃飯。」
江景說好,落座,開電腦。
我手搭上他椅背,倚靠在一旁,看了看窗外昏暗的天,想說要不把叔叔阿姨叫回來算了,余光卻瞥見飄窗旁的地毯上畫著一幅畫。
或許那也不叫畫,是用一粒粒的貓糧拼湊而成的拼圖。
我「靠」了一聲,晃晃江景的肩膀示意他看。
他回頭,也呆住了。
貓糧拼湊出一幅男生女生接吻的圖,不需要怎麼費力就能辨別,男生是他,女生是我。
江景上前捻起一粒聞了聞,我鼻尖霎時嗅到一股雞肉味,他說:「是我給小花買的貓糧。」
這一天沖擊連波襲來,我都快不會反應了,我問:「那這是什麼意思?」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