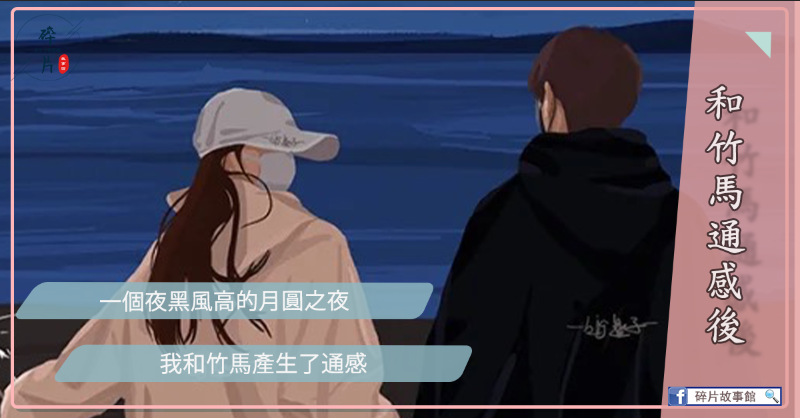《和竹馬通感后》第2章
我心不甘,我意難平,我一再追問江景他喜歡的人到底是誰,可每當談到這個話題,他就跟鋸嘴葫蘆般,一聲不吭。
他越不說我就越想知道,我越想知道他就越不說。
簡直可惡!
一節通識課結束,我追上隔壁教室上課的江景,喊他:「中午一起吃飯啊。」
他皺起眉,像在猶豫要不要答應,我剛要出聲,突然被人從背后拍了一下。
一只手熟練搭上我的肩,親熱地喊:「然妹妹,是過來找我的嘛?」
是社團的陸學長,性格頗為自來熟。
我訕笑著拒絕:「不是的,我來找江景吃飯。」
他熱情道:「沒事啊,一起嘛,這有什麼,多個人多雙筷子嘛。」
這話是這麼用的嗎?
我才要想理由拒絕,就感覺肩上那只手被撥開,眼前是冰冷著一張臉的江景:「不是吃飯嗎?還不走?」
他抓上我的手腕,力道有些大,走出兩步還特意回頭:「你別跟過來。」
走出一段距離,江景松開了我。
我不自在地揉了揉手腕,湊上去跟他搭話:「哇,你剛才抓我那一下,我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很膈應?」他擰著眉。
「也沒有吧……」我模糊回答著,也說不上來是什麼感覺。
他沉默一會兒,說:「以后能不能別讓男生碰你?」
我眨眨眼。
他說:「那人剛才搭你肩那一下,我很膈應。」
我默默腹誹,只是搭個肩而已,直男這都受不了的嗎?
過會兒想起正事,我追上去:「你還沒告訴我你喜歡的是誰?」
他沉默半晌,停步,看著我:「喜歡你。」
我一愣。
繼而心底慌亂,面上不覺帶上幾分求饒的笑:「你別開玩笑了。」
江景思索片刻,認真點頭:「嗯,我在開玩笑。
ADVERTISEMENT
」
我些許悵然,又問:「那你到底喜歡誰?」
他還是那句:「喜歡你。」
「……」我不好奇了。
夜晚躺在宿舍的床上,我還在想江景那張撲克臉,突然聞到燒烤的香。
我掀開床簾,興師問罪:「你們誰背著我吃燒烤了?」
其他室友都在床上玩手機,根本沒人吃燒烤,甚至都沒在吃東西。
而宿舍的門窗緊閉。
我再嗅了嗅,仍舊能聞到,香味濃郁。
腦中閃過一個驚駭的念頭,我給江景發去消息:【你們宿舍在吃燒烤?】
他回得很快:【你狗鼻子啊你?這麼遠都能聞見?】
【……】不是我狗。
是我和他可能又通了嗅覺!
5
解鎖嗅覺這件事是我和江景始料未及的。
畢竟互通身體感覺就已經夠磨人。
有人碰他我知道,有人碰我他知道,雙重觸覺雙份敏感,時常分不清到底是誰在被碰觸。
而且這都算不上麻煩,最麻煩的是洗澡。
十月中旬,天還熱著,一天不洗渾身難受。
未免尷尬,我和江景商量以同步的方式來洗澡。
到了某個點一齊進浴室,對著身體不管不顧一通擦洗,即使也能感受到陌生的觸覺,但可以洗腦成是自己在洗。
但思維總是沒那麼聽話。
我偶爾會生出「我是在幫江景洗澡,而江景在幫我洗澡」的旖旎錯覺。
想到這兒,我就覺得對不起我和他十幾年的革命友誼。
「啪」一聲迅速給了自己一巴掌。
江景那邊洗澡的動作停了。
倒是沒像當初那樣打回我,只是淺握住他的手腕。
我同時感受到手腕上他的力度,像他在握著我、阻攔我一般。
互通身體感覺已經這樣艱難且難熬,沒想到現在還互通嗅覺。
ADVERTISEMENT
或許現在還不是最嚇人。
嚇人的是未知的以后。
我們能在毫無征兆的前提下,先后通了身體感覺和嗅覺,保不準以后會不會連視覺聽覺味覺都一起通了……
但這樣實在太可怕,也過于悲觀。
我和江景還是更愿意相信會在以后的某一瞬突然恢復正常。
我和他試著適應互通嗅覺后的生活。
他能憑借嗅到的味道判斷我和男生還是女生待在一起。
我也能憑借嗅來的味道判斷他在哪個食堂,順便喊他幫忙帶一份晚餐。
但江景總說我這兒有股香味擾得他一晚上睡不好。
我不愛噴香水,也沒有使用香薰的習慣,便懷疑他是不是聞錯,他卻說不可能聞錯,每晚睡覺都能聞到。
他言之鑿鑿,我卻嗅不到,隱晦求助于室友,室友分析這暗香可能來自我身上。
是女兒香。
這結果更扯淡,我不信,開始懷疑這香來自家里帶來的被套,我媽愛用熏香。
為解決江景的睡覺困擾,我躺在床上幫江景購買熏香,耳邊意外傳來男生說話的聲音。
我摘掉耳機,還是有聲音,但那聲音顯然不是出自我們宿舍。
那聲音在說:「江景,你到底喜歡她什麼?」
我瞬間明白這聲音出自江景宿舍,而我和他可能又通了聽覺,但我竟然沒太在意。
滿腦子是即將聽到的小秘密。
江景的聲音響在耳畔,低沉悅耳:「我哪知道我喜歡她什麼。」
「漂亮?可愛?說不太出來,反正感覺她什麼都好,」他說,「就是不喜歡我,這點不好。」
「而且她有點傻……」
我凝神側耳,還欲細聽,突然聽見室友喊我的名字。
「安然,借你耳機用一下!」
我遲緩地應:「——啊,在桌上,你拿。」
待這小插曲過去,耳邊再沒了江景那邊的聲音,像是恢復了安靜。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